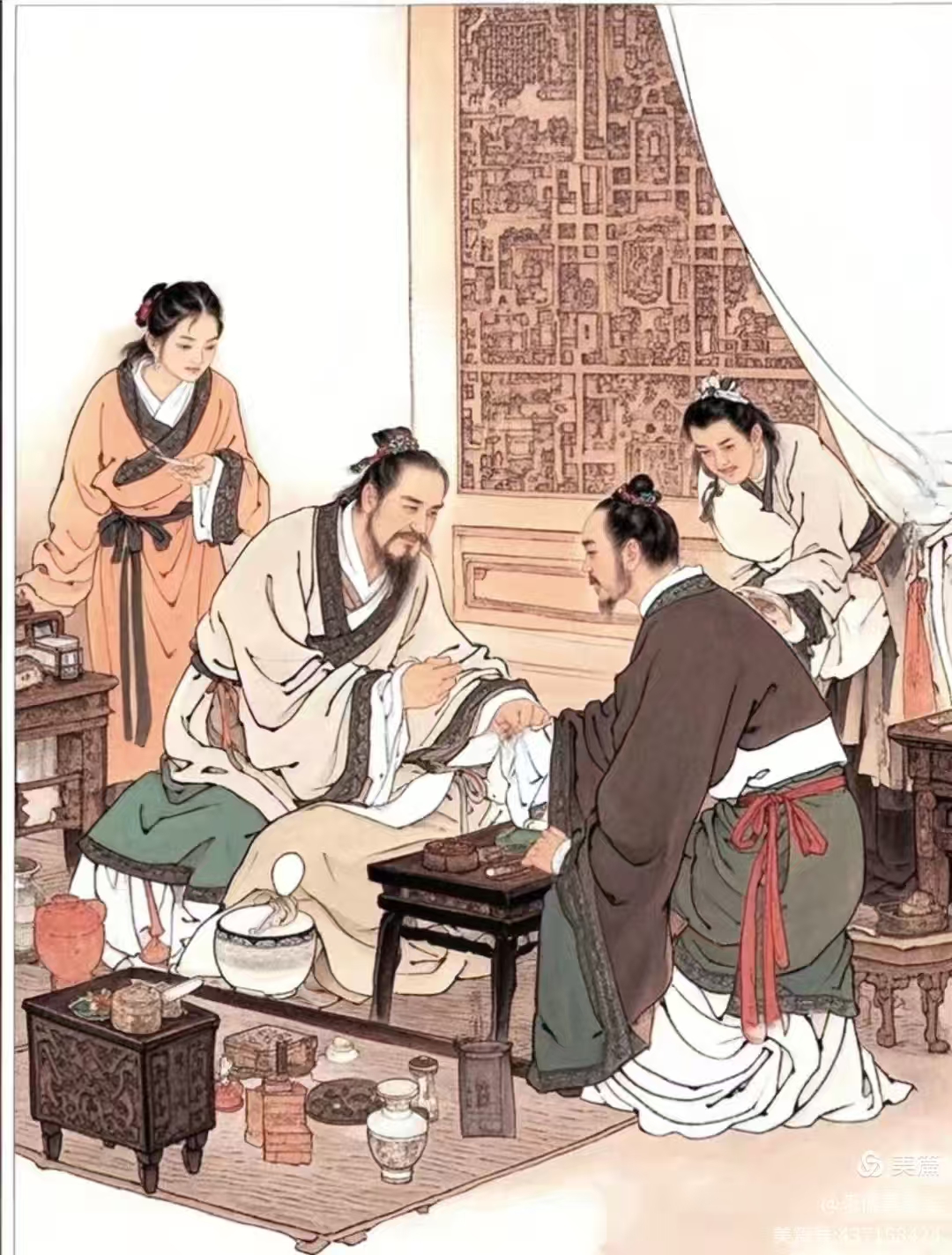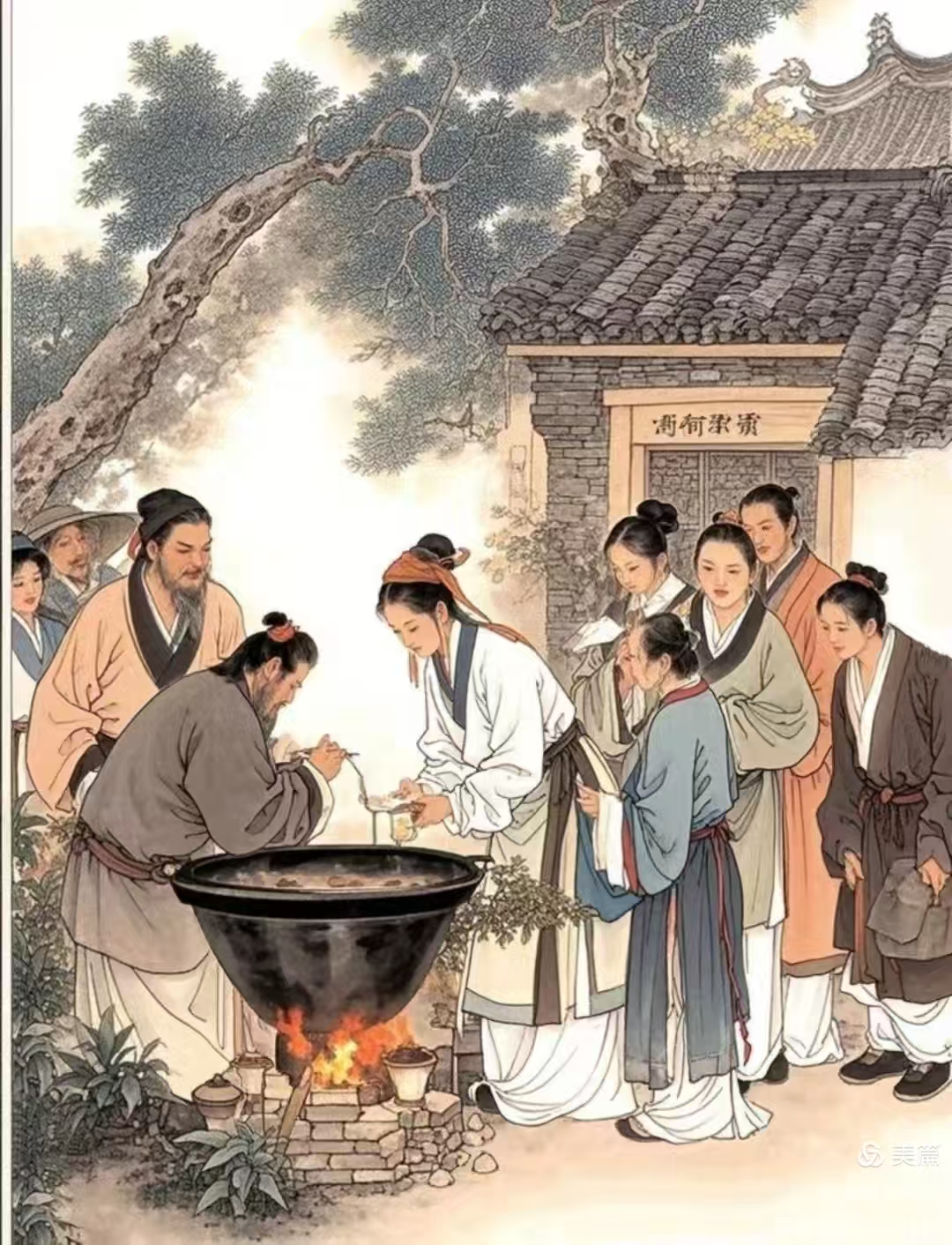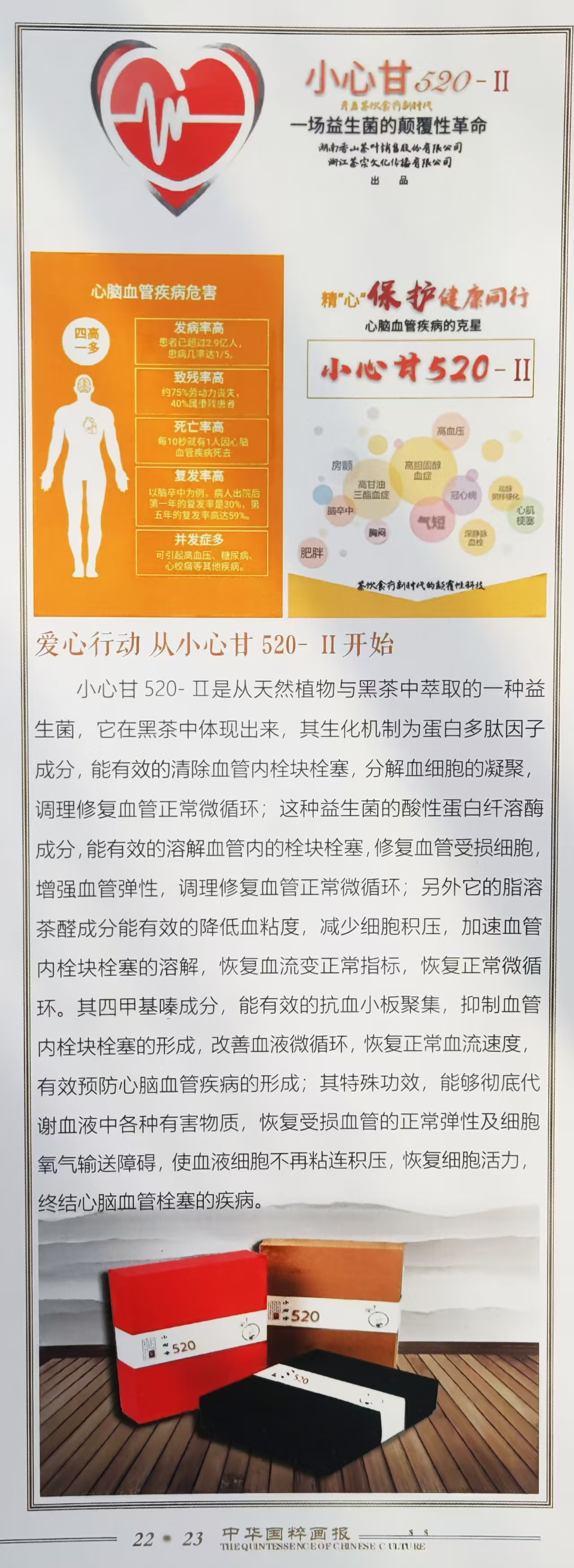第六章:
口眼斜 厥症色
面瘫时 忌辛热
六经余 从汗解
邪所凑 不轻泻
七情伤 心失策
饮食过 吐致格
肥中者 祛湿热
久滞下 人参克
栓塞症 附姜可
华陀方 切八个
目眶颤 肝脏涩
归脾加 逍遥乐
讲二案 治法特
有血厥 妇多得
治寒厥 四物也
加附桂 必起色
治热厥 六味折
中薄厥 蒲黄喝
四肢冷 乃精绝
热煎厥 固本学
尸厥者 流苏祛
痰厥来 姜附合
蛔厥者 乌理责
按阴阳 互补和
葵此论 大医惪
注译:
上一章我们已经把中风讲了,这一篇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口眼 斜和厥证。首先我们先讲讲一下口眼斜。

《灵枢经》里边提到“足阳明之筋”,“筋”就是指的肌肉。足阳明胃经在面部,从面颊部嘴边经耳前上去,如果面颊部的肌肉中了寒邪,“则急引颊移口”,寒主收引,面颊部肌肉收缩就把嘴给拉歪了,如果是热,面颊部肌肉就松弛、瘫软。“纵缓不能收”,“不能收”就是不能够收缩,“故僻”,也就是肌肉瘫痪,往一边歪。这就是《灵枢经中》讲的口眼斜了。“是左寒右热,则左急而右缓;右寒左热,则右急而左缓”,脸往哪边歪,取决于寒在哪边,就往哪边歪。“故偏于左者,左寒而右热;偏于右者,右寒而左热”,通过观察脸往哪边歪,我们来判断哪边有寒、哪边有热。其实这只是古人关于口眼斜的一种解释。
口眼斜要关注的是,“不可径用辛热之剂”,也就是当你见到面瘫时,不要随便去用辛热之剂,这应该是古人的经验之谈,一定要记住的,这是重点,故上文曰:面瘫时,忌辛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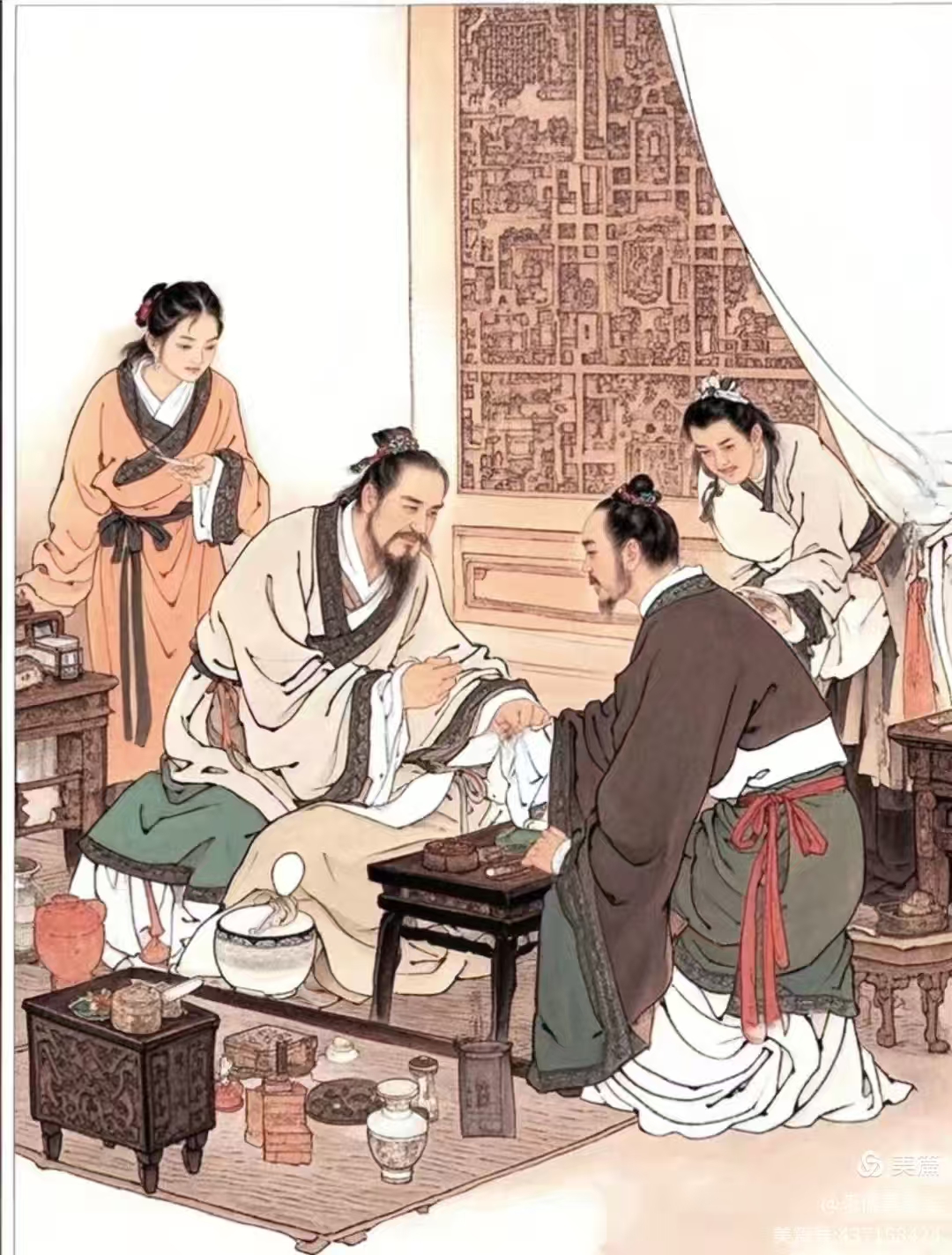
只有中了风邪才会有口眼斜的症状,不能完全把风邪归结为受风。但是,前面提到不能用热药,因为风为阳邪,所以用热药治疗效果不好,这个是肯定的。“盖火胜则金衰,金衰则木盛,木盛则生风”,这是用五行生克的道理来解释的。“《素问》书中曰:诸风掉眩,支痛强,直筋缩,为厥阴风木之气”,在临床上见到了风、掉、眩、支痛、强直、筋缩,都是厥阴风木之气,都与肝风相关。在自然界,从大寒开始阳气逐渐开始回升,直至小满。小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小麦充盈饱满的时候。“风木君火二气之位”,风和火管的是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一段时间表现出来的是风、火之象。“风主动,善行数变。木旺生火,风火属阳”,夏天之前这一段,整个阳气是回升的。“多为兼化”。那如何理解兼化?也就是风和火往往两个同时存在,或是一前一后,所以说风邪为病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火象,火邪有病的时候也会有风象。当此之时,小续命汤可用乎”,小续命汤在《金匮要略》里边提到过,实际上最早应该是在《千金方》里,后来补到《金匮要略》里边去了。一个风寒的基本方,可以根据三阴三阳出现的情况来进行加减,但不一定完全照搬全方使用。“如太阳无汗,于本方中倍麻黄、杏仁、防风”,也就是把辛散药重用;如果有汗怕风,那就用小续命汤,里边“倍桂枝、芍药、杏仁”,这就是告诉你具体怎么来加减。“如阳明无汗身热不恶风”,加“石膏、知母、甘草”,如果是“有汗身热不恶风”,方中就加“葛根、桂枝、黄芩”,“如太阳无汗身凉”,如果是太阳病的表现,“无汗、身凉”就加“附子、干姜、甘草”,如果是“少阴经中有汗无热,于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这就是小续命汤怎么加
减来使用,讲得还是比较具体的。我认为这一段应该给予关注,想用好小续命汤,就要把这段话记住。

“凡中风无此四证”,刚才上面提到的四种加减的情况,“无此四证”“六经混淆”,也就是三阴三阳分不出来到底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系于少阳、厥阴,或肢节挛痛,或麻木不仁”,如果是这样,“每续命八两”,就是用续命汤原方八两,再“加羌活四两、连翘六两”。这讲的还是中风的治疗,“小续命汤”是古人最早治疗中风的一个基本方。
尤其是病人出现中风、半身不遂的时候,古人认为有了“风”就加“羌活”。我们从中西医结合角度来讲,中风就是脑血管有病了,这种情况下用羌活,提示我们什么?首先它能够改善脑部血管的病变,对梗死性的中风是有效的,那对于脑动脉硬化有没有效?实际上都已经研究得非常清楚了,有医家已经证明羌活是一个治疗脑动脉硬化、脑缺血非常有效的药。我忘了是哪位医家,他专门就用羌活改善脑供血。再一个加连翘,现在一说中风,谁去加连翘?但是如果考虑到它是感染引起的,由于感染引起血管的病变,进一步导致梗死,或者是出血,这时治疗感染本身就可以改善疾病。所以可以这么来理解、解读。总而言之,这些经验才是真正需要记住的。“此系六经有余之表证,须从汗解”了。好是大便下不来,尿出不来,就用三化汤、续命汤,“或《局方》麻仁丸”,这都是通利二便的药。“虽然,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上面所讲都是祛邪的办法,但是毕竟是“邪之所凑”,其气是必虚的,所以“世间内伤者多,外感者间而有之,此方终不可轻用也”,很多的病都是在气血阴阳虚弱的基础上,然后受的邪,而此方完全是祛邪的方,不能够轻易地去用,除非是虚不重可以用这个方子,这是作者的观点。

七情所伤是许叔微讲的,经曰:神伤于思虑则肉脱”,也就是伤神,即思虑过度就会消瘦。“意伤于忧愁则肢废”,四肢不能动。“魂伤于悲哀则筋挛”,四肢伸不开了,“魄伤于喜乐则衰槁,志伤于盛怒则腰脊重,难俯仰也。”这一段讲七情所伤造成的中风,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生气着急、过度高兴出现问题,至于说哪种情志的损伤一定和“痉挛’“肉脱”等相联系,我认为这种对应必要性不大,这是一个纯理论的讲法。
情志的变化往往迅速导致气机的逆乱,它不走寻常道,往往走向它的反面,导致“牙关紧急。若作中风误治,杀人多矣”。注意这儿讲的“中风”指的是感受外邪,不是表现出来半身不遂的这种中风,所以不能按这个治。“盖中风者,身温且多痰涎”,注意《医贯》里边讲到的中风,始终在强调中风是有“身温”的特点,若“中风”,身体是不的,如果是气厥导致的,就会身凉且无痰,这是纯精神性的。“宜苏合香丸灌之”,要用“苏合香丸” 治疗中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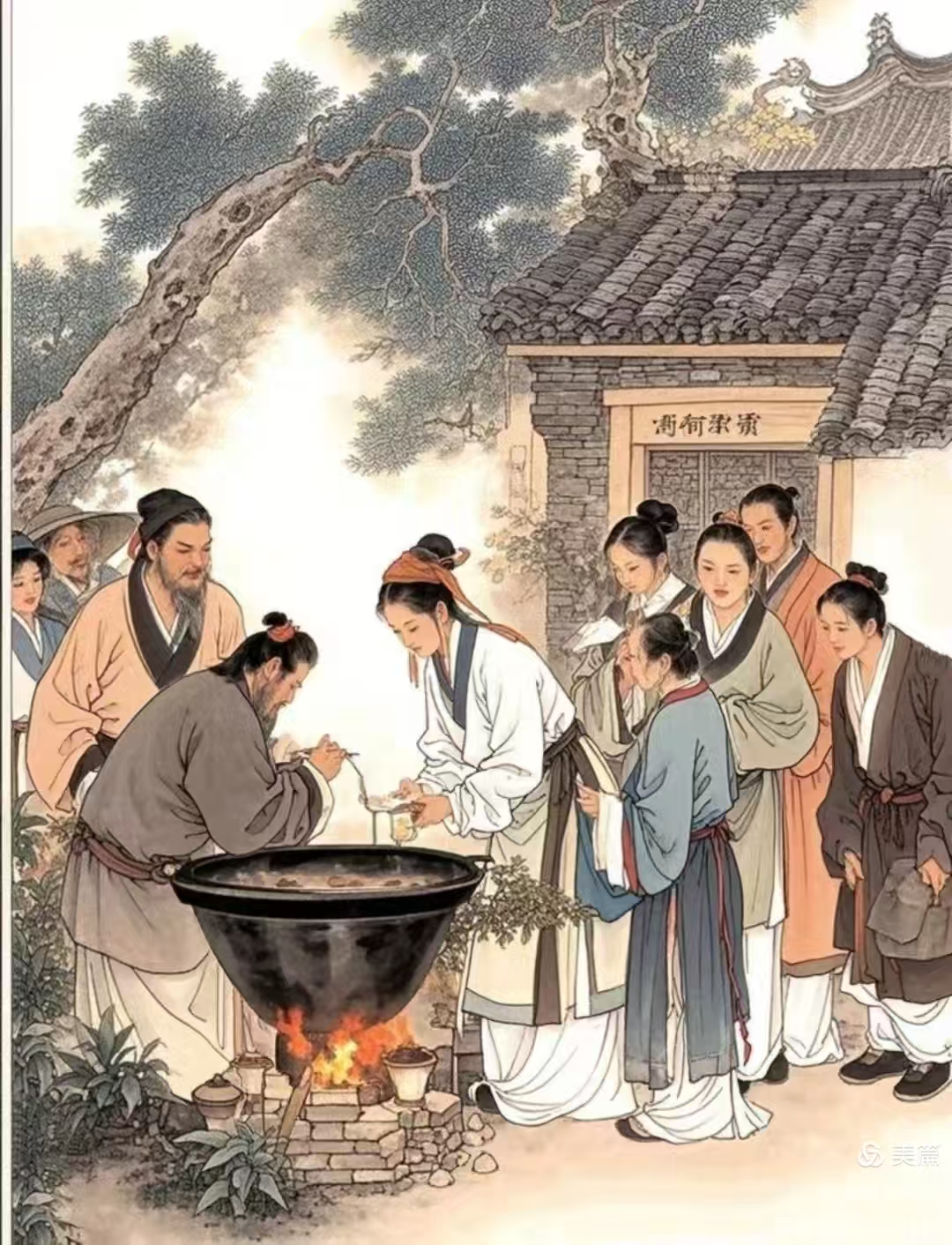
如突然不能说话,病人应该还伴随有意识的丧失,就是一个心源性的脑缺血,是不是这样?这肯定是个心律失常,比如传导阻滞,脉摸不着了,时间很长,然后脑子缺血,肯定不会说话了。“虽不治自己”,为什么?因为一会儿心律恢复正常,各种症状就都好了。心跳间歇较长,会出现这种情况,人有时会在生气时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心律失常。
王节斋讲我们在临床上会见到,饮食过多,突发昏迷不醒。“若误作中风、中气治之立毙”,如果当成中风,或者是七情致病,按这个来治疗就会死亡。即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探吐”,让他吐出来,“食出即愈”。这实际上还是心源性脑缺血,但原因是过量饮食,急性胃扩张引起的迷走神经张力增高,出现这种情况,更应该用吐法。“详见《格致余论》木郁则达之条下”,《格致余论》这本书里,“木郁则达之”这一篇里有论述。“已上二条论,当与厥门互看”,意思是“饮食醉饱”和脉象这两条要互相参照。

肥人善饮多急性中风,这种病的机制是什么?“气盛于外”,外边看起来形盛,“而歉于内”,内在的气又不足,再加上湿热,酒助湿热,由此致病。怎么治疗?“须用六君子,加煨葛根、山栀、神曲而治之”。我们现在很少这么用,但是赵献可讲要这么用的,他认为内虚,所以要用六君子来补气,健脾和胃,再加上有湿热,所以用葛根解酒,因为这人是平素肥胖善饮,“酒饮湿热之证”,所以用了葛根,然后加了栀子去湿热,加神曲消导。这是他治疗肥胖中风病人的治疗思路。
“有一人久病滞下”,“滞下”是什么?就是慢性痢疾,拉得不顺畅,里急后重,这是“滞下”。“忽一日昏仆”,突然有一天昏迷。“目上视”,两目上视,“注而汗泻”,“没注”就是小便失禁,“汗泻”就是出汗,拉肚子。大小便失禁,且汗又多,这就比较危重。假如这样的病人来就诊,我们该如何考虑?这个病人应该是一个脑栓塞,房颤、栓子脱落。平时又有“滞下”,什么意思?他又有感染,胃肠黏膜破坏了,有害物质就进入血液,破坏血管;或是病原微生物进入血液形成菌栓,突然掉下来堵住脑部血管。其实我们刚才分析得很清楚了,治疗消化系统的问题,防止血栓形成就可以。那慢性消化道感染的病人又兼有房颤,出现了脑栓塞,怎么治疗?要灸气海,吃人参。此处给我们启发最大的当是人参,现在栓塞性疾病的治疗我们常用抗凝药,防止梗死面积加大,一味人参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人参具有很好的抗栓、溶栓的作用。《贾海忠中医体悟》中讲过,服用人参易上火,上火的表现就是出血,出血意味着什么?出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容易使溶血、纤溶功能亢进,使血小板免于聚集。而且人参本身是治疗消化道疾病的基本药,比如四君子汤。它既能保证胃肠黏膜功能又能够防止血液的凝固,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案例如果我们能读到这个份上,那在临床应用的时候就敢放胆去用人参。而且这种治疗极其简单,一味人参就治好了。这类栓塞性疾病,会卧床,卧床过久静脉系统会形成血栓。稍微一动,栓子脱落,若到心房里边就顺着动脉走,可以引起肺梗死。既然人参有这个作用,肺梗死能不能用?我们从这里引申出来,肺梗死病人要大量地、赶紧地用人参!这里我们还举例了“华佗救阳脱方”,“用附子一个,重一两,切作八片”。我没见过大附子有多大,没有去考察过。“重一两,切作八片,用白术、干姜各五钱,木香二钱,为末,煎。先用葱白一握炒熟,熨脐下,次候药冷,灌服,须臾又进一服”。注意,这里是分两次的,一个是先用葱白捣烂后炒熟敷在肚脐底下。“次候药冷”,就是药熬好后放凉,然后给他灌进去。停一会儿,再给喝一次。这个须臾是多长时间?我们古代都是有记载的,须臾是48分钟。故上文讲久滞下 ,人参克,栓塞症, 附姜可。华陀方 切八个。
这个又是案例,我现在越来越认为案例教学最好了。把里边的真东西拿出来,那就是实战过的经验。这个案例,“有一妇人先胸胁胀痛”,就是整个胸胁的胀痛,“后四肢不收”,四肢没力,“自汗如雨”,就是大汗淋漓,“小便自遗,大便不实,口紧目“目闰”,发“顺”音),饮食颇进。十余日”,我们分析一下这是什么病?我们从现在西医临床来看,这个病人应该是消化道疾病,大便不实,一直拉稀,伴随大量出汗,津液大量丢失,然后出现低钙,就表现为口眼也在动,也就是肌肉兴奋性增碍、小便失禁,这样我们就把病位定了。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中脏”的病,请薛立斋来治疗。薛立斋也是一个古代名医,这是薛立斋看的病例,赵献可引用了。“曰:也”,就是说这不是中脏,“若风既中脏,真气既脱,恶证既见,祸在反掌,焉能延至十日”?也就是说这个病还不是中脏,没那么重,虽然看上去还挺厉害。“诊其脉左三部洪数,惟肝尤甚”,左脉是洪数脉,显然邪气较重的。“乃知胸乳胀痛,肝经血虚,肝气否塞也”,他根据这个来判断胸胁胀痛是肝经病变,按我们中医理解起来没有任何障碍,但是从西医角度来讲,就不那么好理解。“四肢不收”,肝经血虚不能养筋,也可理解为肝主筋。其实按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因为严重的消化道疾病,营养不良而出现慢惊风。此体阴用阳,肝体不足不能够履行它正常的功能,表现出来一派热象。“大便不实,肝木炽盛,克脾土也”,这是从五行来分析的,“遂用犀角散四剂,诸证顿愈”,犀角散,清热凉血,清肝火,凉血热,用四剂以后就很好了。“又用加味逍遥散调理而安”,用了犀角散四剂以后,又用了加味逍遥散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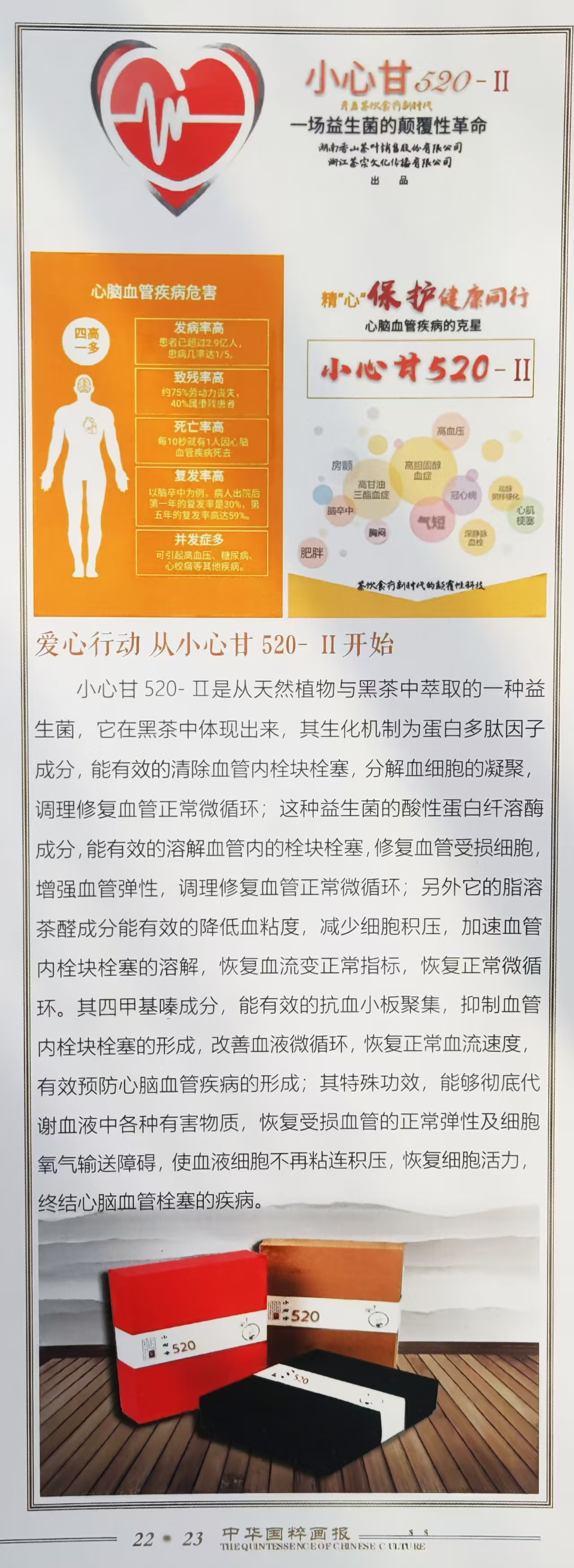
得了中风,前面讲的都是吃药,有个病人给不了药,不能说话肯定就张不开嘴,喝不了药怎么办?大夫就用黄芪、防风,煮了以后让她躺在那里熏疗,熏了一天好了。“卢州王守道风噤不能语”,也是不能说话,嘴张不开。王克明医生“令炽炭烧地”,用炭烧地,在烧热的地上面再撒上药,“置病者于其上”,把病人放在上边,与熏疗也差不多。“须臾小苏”,过了一会儿他就清醒些了,原来是不能语,实际上是昏迷,现在好了。“已上二例,病至垂绝,汤液不及,亦治法之变者也”,做医生的不能只知道开汤药,其他方法也要学习,赵献可告诉大家,还是要多学点办法。
前面讲了口眼斜,那么后边讲的是“厥”。先讲血厥”,此妇人多有也。这就是《金匮要略》中讲的产后有郁冒,因为产后易失血过多,导致血容量少。这讲的是出汗过多,出汗过多血容量也是减少。当血容量减少的时候,脑子供血供氧就不够,就会出现相当于休克的表现。“阳气衰乏者,阴必凑之”,阳气不足了,阴就要往这儿来凑,“令人五指至膝上皆寒”,从五个脚趾至膝上都寒,“名曰寒厥”,此宜六物附子汤”。热甚则循三阴而上逆,谓之热厥”,“热厥”用什么方治?用“六味地黄丸主之”。“肝藏血而主怒,怒则火起于肝,载血上行,故令血菀于上。是血气乱于胸中,相薄而逆也,谓之薄厥”。薄厥用什么方子?用“蒲黄汤主之”。
“诸动属阳,故烦劳而扰乎阳,而阳气张大。阳气张大,则劳火亢矣。火炎则水干,故令精绝”。“阳气张大,则劳火亢矣”,表现出来的全是一派热象。热得厉害,水就容易干,“水干精绝”,因为中医讲的精还是属于阴,阳气过度的时候,耗伤的是阴精,四肢冰冷,即“精绝”尔。

“水益亏而火益亢”,就容易理解了,这叫“如煎如熬”。这种病叫“煎厥”。“煎厥”用什么?用“人参固本丸主之”,“人参固本丸”是补益人体元气的,元气足这个火就容易去,这也是在李东垣的书里说的“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所以还是要用补气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种热。还有气和形之“纽”,“络”都被打破,机体不相顺接,不能够协调一致。“故令暴厥如死,名曰尸厥”,这都是从外感受到的、伤人迅速、置人死地的邪气。用什么办法?“二十四味流气饮、苏合香丸”,芳香避秽。“寒痰迷闷,四肢逆冷,名曰痰厥”,如果是痰比较多,就叫痰厥,是四肢凉,叫“痰厥”,用“姜附汤主之”。“胃寒即吐蛔虫,名曰蛔厥”,用“乌梅丸加理中汤主之”,这个大家也比较熟,在《金匮要略》里边专门讲过。赵献可在他的学术观点说“余按常病”,“常病”是什么病,不是刚才讲到的这些。第一个是“阳厥补阴,壮水之主”。第二个是“阴厥补阳,益火之源”。他把证分成两个,阴厥和阳厥。除了前面前人的划分和相应的治疗以外,说“阳厥”应该用补阴的办法,“壮水之主”。我认为他前面讲的只要属于阳性的“厥”,都算是“阳厥”,用养阴的办法来治疗,这与前
面提到的道理是一样的。“阴厥”就补阳,“益火之源”,“阴厥”就凉,就要壮阳、补阳。他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他讲的“阳之根为火,阴之根为水”,水火是命门,最终还是回到他的学术观点上来讲肾间动气。那么阴、阳按这来划分,用这两个原则来指导,与伤寒怎么区别?伤寒的阳厥,“用推陈致新之法”,“阴厥,则用附子理中”。这是伤寒里边的两厥,也是分阴厥、阳厥,伤寒的“阳厥”就用推陈致新,如大承气汤,四肢厥冷要用泻下的方法,因为是阳气郁闭在里,所以要推陈致新。最后还是归结到我们《黄帝内经》里边讲的诊断,首先要“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大方向不要错,然后有具体的治疗方法,更细致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中风这一篇内容比较多的,因风为百病之长,所以它导致的病比较多,尤其是有一些类似风的疾病,又合在一起比较,内容非常丰富。赵献可把具有代表性的这些医家的观点,以及自己的观点总结形成了这篇文章,以供医者借鉴运用可谓是大医惪,这个惪同“德”,用此惪,无非强调医者要重德也,须直心以示,不可以利偏废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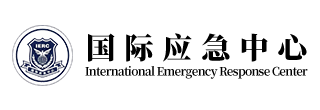

 全国免费客服电话 400 8749 119
全国免费客服电话 400 8749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