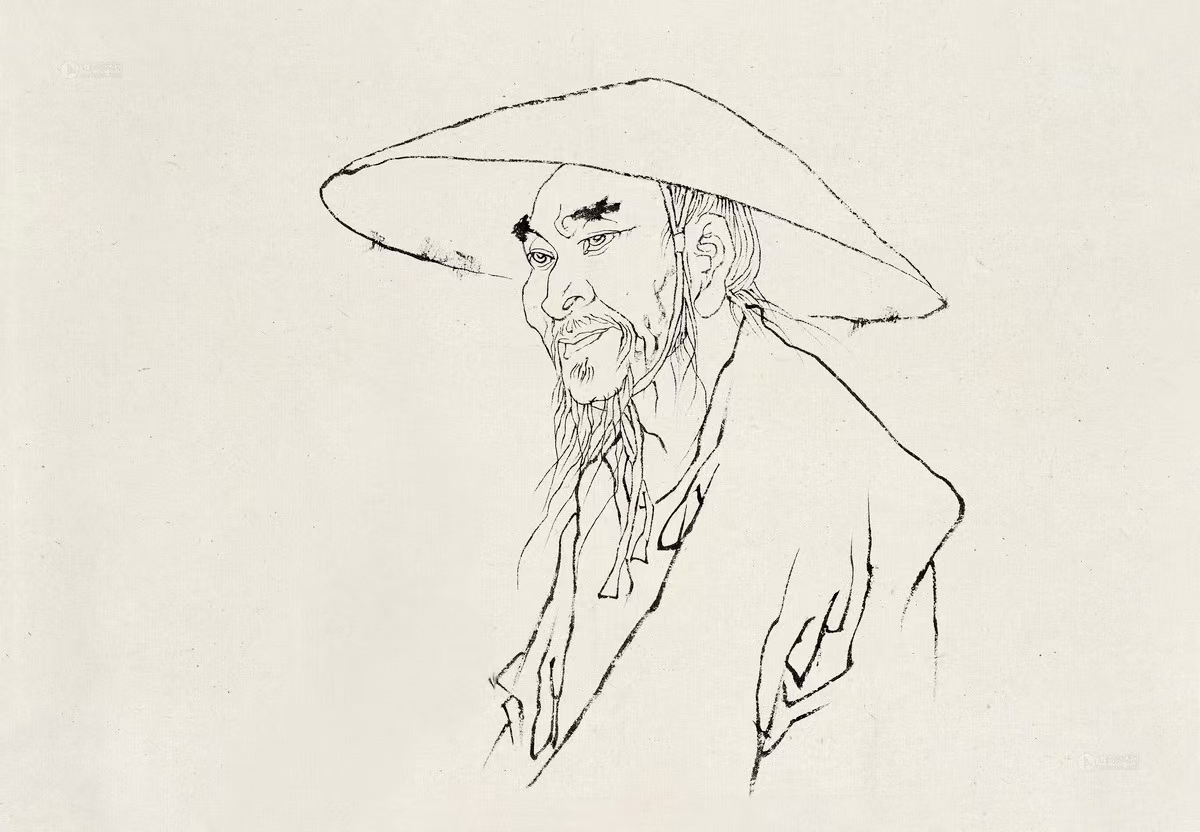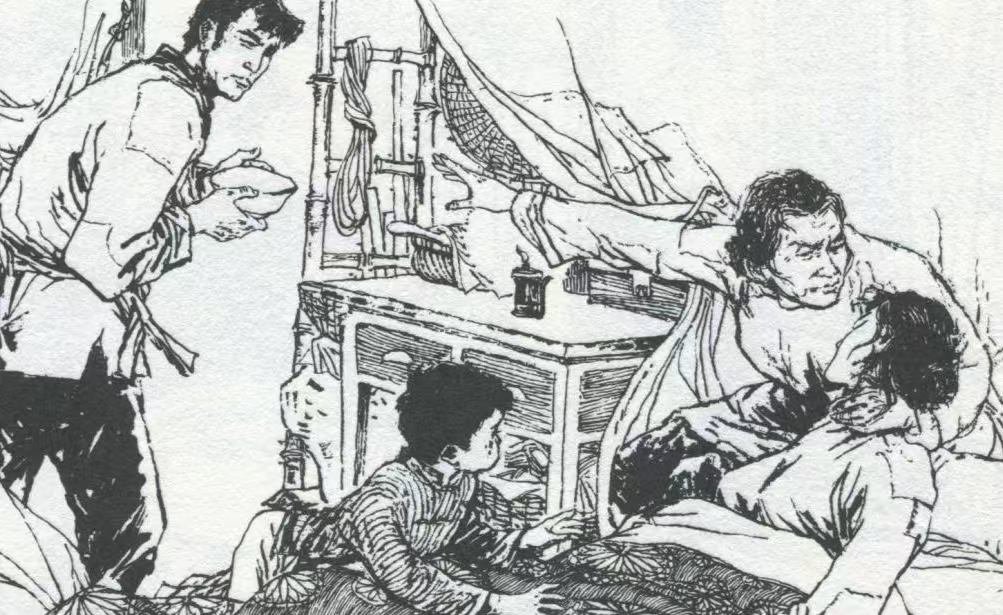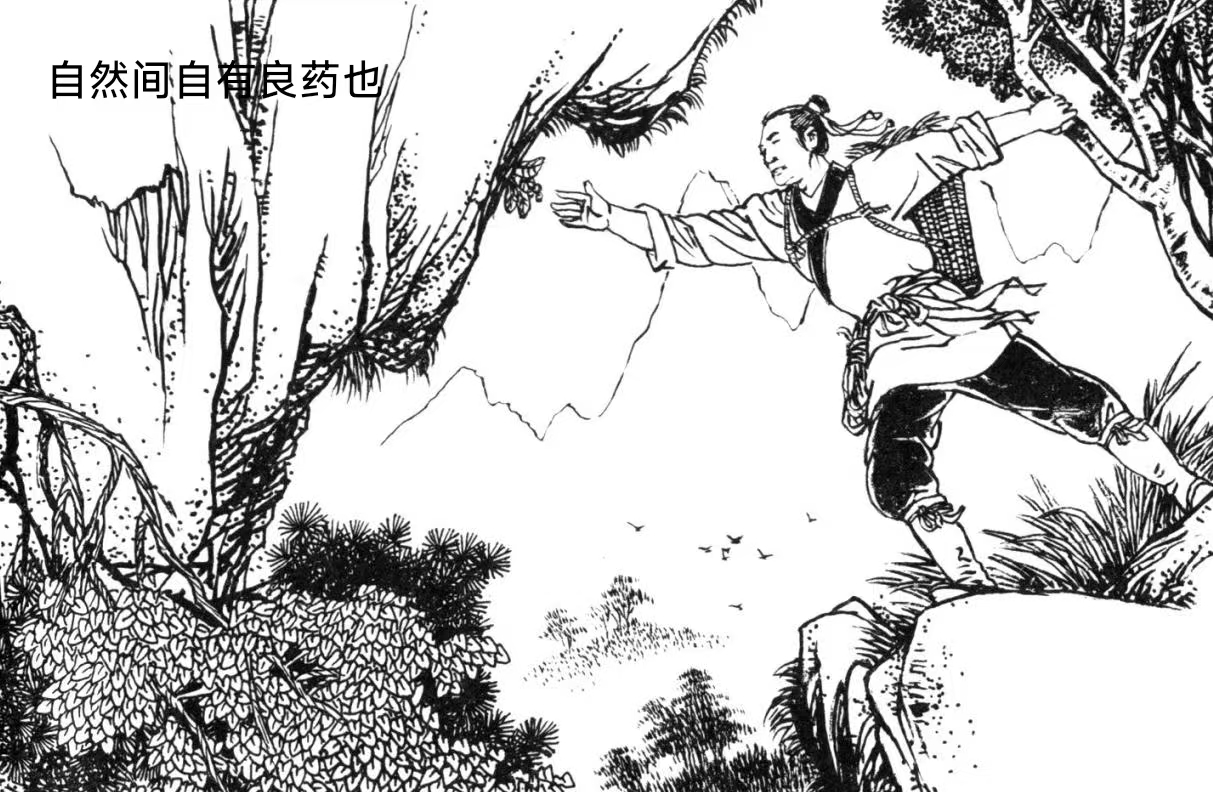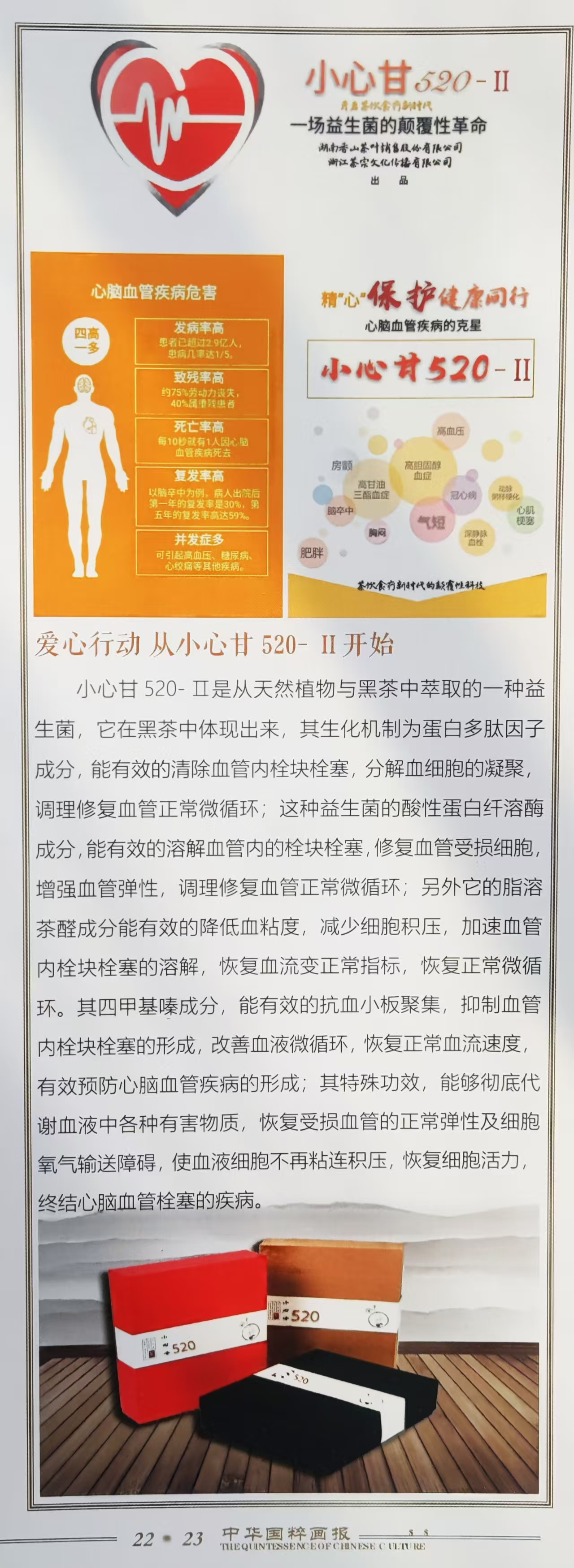第十四章:
桂附地 即八味
脾肾虚 其可医
其炮制 讲点滴
熟地黄 真怀地
圣惠方 内讲其
味加减 各有易
加五味 乃都气
减桂附 是钱乙
益济阴 启原机
易老云 西北剂
葵曰益 肺肾脾
宋至今 多衍义
凑多效 治诸异
慢性肝 医难题
异同论 真神奇
注泽:
桂附地黄丸就是八味丸,“八味丸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也就是脾肾两虚,而且是阳虚,就是脾肾虚寒。只要有脾肾虚寒的,就可以用桂附地黄丸。我们以前说肾阳不足、肾气虚用八味地黄,赵献可是脾肾虚寒用八味地黄。他的症状是脾阳不足,不想吃饭,大便不实,偏软,它不干。或者是有“下元衰惫,脐腹疼痛,夜多溲溺等证”,除了脾胃虚寒的症状以外,还有下元疲惫,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肾气不足,表现是脐腹疼痛,就是肚脐周围疼。再一个就是夜尿多,这是金匮肾气丸的适应证,八味丸的适应证。
在这里这个方的药物组成以及炮制我们简单地说一下,“熟地黄八两,用真生怀庆”,一定是真正怀庆府的生地,我们说四大怀药,指的是怀地黄,用真的,而且是生的,用酒洗,用酒泡一宿,然后再把它放砂锅上蒸半日,晒干,然后再蒸,再晒,九次为度,就是要九蒸九晒,把生地变成熟地,这是生地变成熟地的一个最规范的炮制方式,一个经典的炮制法。山药实际上也应该是怀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这些都没有特殊的,对生地讲得比较细,一定要用怀地黄。

“《圣惠》云:能伐肾邪,皆君主之药,宜加减用。加减不依易老亦不效”,在《圣惠方》里边说八味地黄丸,它是伐肾邪的,就是治肾病的,里边的药都是君主之药,也就是他用的这些药,都非常重要不能缺少的,使用的时候宜加减,这都是《圣惠方》里边谈的。
这《圣惠方》就是《太平圣惠方》,方书,100卷。乃北宋王怀隐、王祐等奉敕编写。自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至淳化三年(992年),历时14年编成。其书为我国现存公元10世纪以前最大的官修方书,汇录两汉以来迄于宋初各代名方16834首,包括宋太宗赵光义在潜邸时所集千余首医方,及太平兴国三年诏医官院所献经验方万余首,经校勘类编而成。书中对此还提到说“加减不依易老亦不效”,什么叫不依易老亦不效?易老是谁?是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易水学派。也要根据他们的来加减,要不然效果也不好。“今人有加人参者”,现在有人用八味地黄丸加人参的,他说人参是脾经的药,是入脾的,根本就不入肾,也就是说想加人参,加强它补肾的作用,起不到这个作用。“有加黄柏、知母者,有欲减泽泻者,皆不知立方本意”,在后世有的是加黄柏,这就是桂附再加黄柏的,有的时候把里边泽泻去掉,说它是泻的,这都是不知道张仲景立这个方子的本意是什么,没明白这个方子。

“六味加五味子,名曰都气丸,述类象形之意也”,就跟取类比象有点类似。六味地黄加五味子叫都气丸。钱氏是指的钱乙,《小儿药证直诀》里边减桂附,名曰六味地黄丸。它是治什么呢?治小儿。“小儿纯阳,故减桂附”,小儿为纯阳之体,生机勃勃,不需要用桂附,所以说就把它给减掉了。 这个钱乙在这里我稍加介绍一下,他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其留有《小儿药证直诀》三卷,记载了23种病症的病理现象及很多方,如上所讲仍六味地黄丸,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小儿药证直诀》一书比欧洲最早出版的儿科著作早三百年,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著作,很了不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小儿药证直诀》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其一生著作颇多,有《伤寒论发微》五卷,《婴孺论》百篇,《钱氏小儿方》八卷,《小儿药证直诀》三卷。现仅存《小儿药证直诀》,其他书均已遗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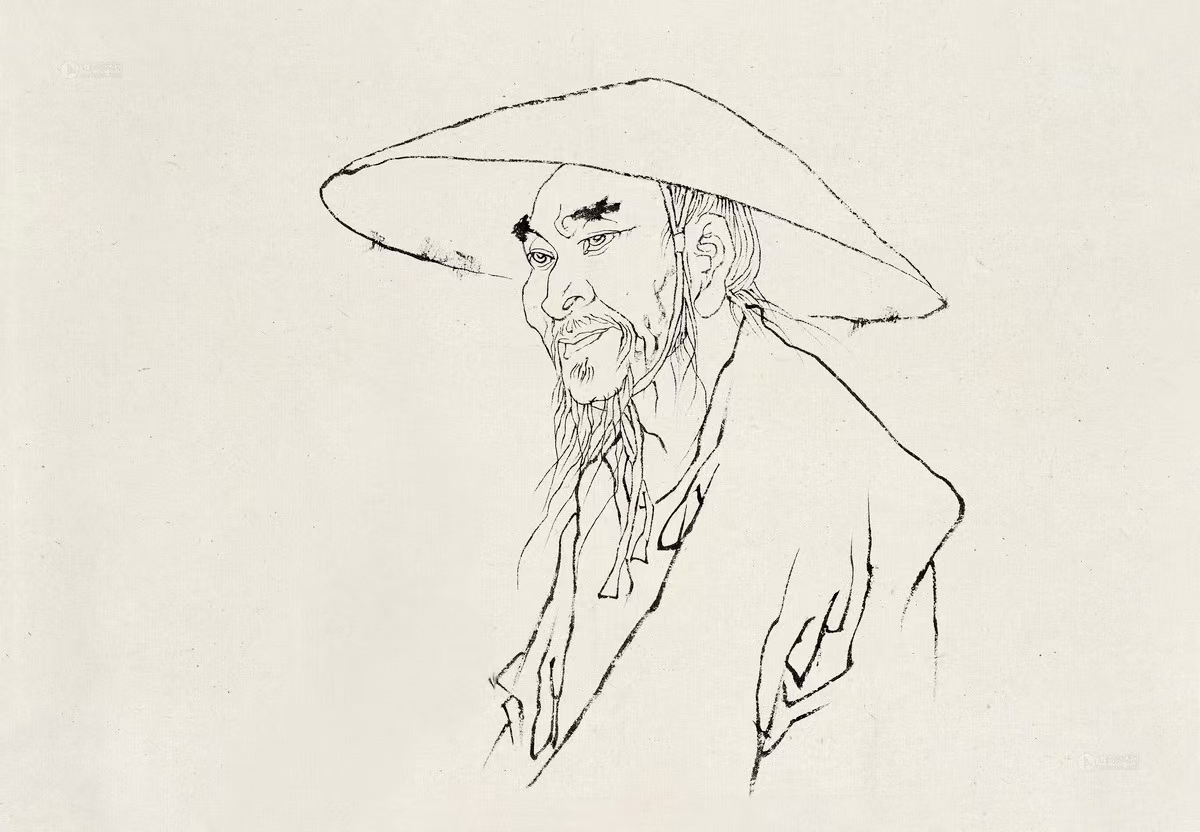
接着书中又讲 “杨氏云: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名曰加减八味丸”,这又是一个医家的用法。这个加减八味丸乃中医方剂名方。其出自《辨证录》卷三,具有滋肾补气之功效。《内科摘要》中记载:大尹沈用之不时发热,日饮冰水数碗。寒药二剂,热渴益甚,形体日瘦,尺脉洪大而数,时或无力。王太仆曰:热之不热,责其无火;寒之不寒,责其无水。又云:倏热往来,是无火也;时作时止,是无水也。法当补肾,用加减八味丸,不月而愈。
又载曰:州同韩用之年四十有六,时仲夏色欲过度,烦热作渴,饮水不绝,小便淋沥,大便秘结,唾痰如涌,面目俱赤,满舌生刺,两唇燥裂,遍身发热,或时如芒刺而无定处,两足心如烙,以冰折之作痛,脉洪而无伦。此肾阴虚阳无所附,而发于外,非火也。盖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峻补其阴。遂以加减八味丸料一斤内肉桂一两,以水顿煎六碗,水冷与饮,半饷己用大半,睡觉而食温粥一碗,复睡至晚,乃以前药温饮一碗,乃睡至晓,食热粥二碗,诸症悉退。翌日畏寒,足冷至膝,诸症仍至,或以为伤寒。余曰:非也,大寒而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阳气亦虚矣。急以八味丸一剂服之稍缓,四剂诸症复退。大便至十三日不通,以猪胆导之,诸症复作,急以十全大补汤数剂方应。
《集验背疽方》亦有载录:有一贵人病疽疾,未安而渴作,一日饮水数升,愚献此方,诸医失笑云:此药若能止渴,我辈当不复业医矣。诸医尽用木瓜、紫苏、乌梅、参、苓、百药煎等生津液、止渴之药,服多而渴愈甚。数日之后,茫无功效,不得已而用此药服之,三日渴止。今医多用醒脾、生津、止渴之药,误矣而其疾本起于肾水枯竭,不能上润,是以心火上炎,不能既济,煎熬而生渴。今服八味丸,降其心火,生其肾水,则渴自止矣。
复《续名医类案》:薛立斋治一男子口舌糜烂,津液短少,眼目赤,小便数,痰涎壅盛,脚膝无力,或冷,或午后脚热,劳而愈盛,数年不愈。服加减八味丸而痊。综上所述可见这加减八味的功效实在是妙用无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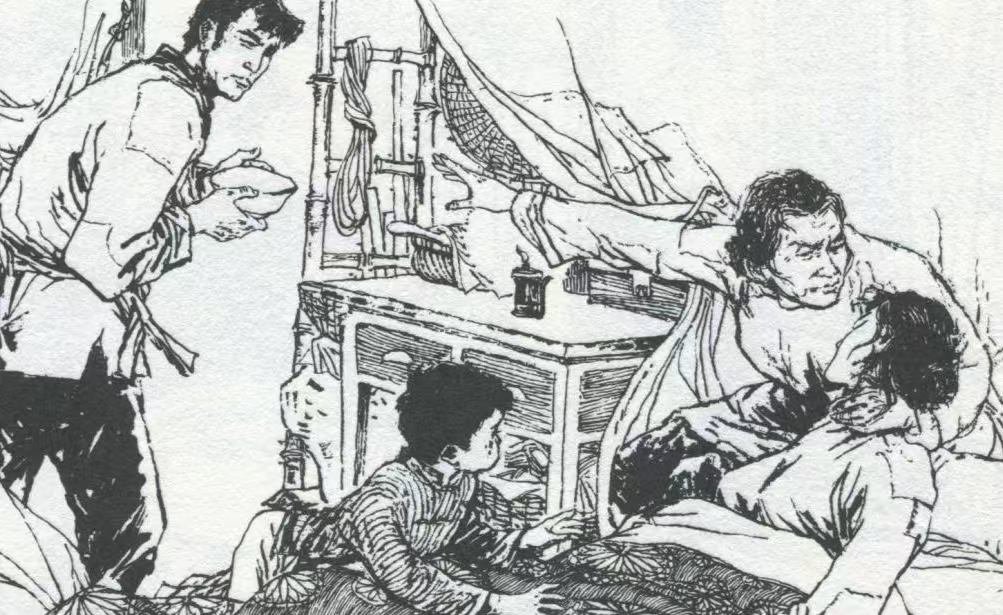
当然也有讲不妙的, “丹溪有三一肾气丸”,就是在朱丹溪书里边有,“独此方不可用”,他就说朱丹溪三一肾气丸不好。“仲景有金匮肾气丸”,实际上这个就是八味丸了。“益阴地黄丸”,这又是一个,“治目病火衰”,眼病有阳气不足的。还有济阴地黄丸,也是治疗目病有火的,这两个方子在《原机启微》里边有。“易老云:八味丸治脉耗而虚,西北二方之剂也”,注意西北二方,是治疗“脉耗”,就是血脉血虚,血脉不足,那么西北二方之剂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西就代表是金,北就代表水,实际上是治疗金、水病变的一个方子,五行、五方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有的时候他们会用东南西北来表示木火土金水,有时候它是变一个说法。“金弱木胜”,金弱指的是肺弱,木胜指的是肝旺,金弱木胜,水少火亏,水少就是五行之水不足,火亏也是指五行之火不足。“或脉鼓按之有力”,脉跳得很有力。“服之亦效,何也”,因为前面讲的这都是虚,但是虚一般是无力的,为什么有的脉很有力用它也有效呢?“答曰:诸紧为寒”,只要脉明显的有力,我们一般都认为这个脉紧是寒,寒的原因是火亏。“为内虚水少,为木胜金弱,故服之亦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解释,赵献可用五行解的比较多,知道这个方子是补益肺肾的,补益脾肾阳气就够了,而且主要是肾阳。
应该说从宋代至清代,这个方剂的适用范围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实际上早已不再局限于儿科疾病的治疗,而是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充分展现了中医“异病同治”的深邃思想。尽管这些疾病的外在表现各异,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肾水不足、肾阴亏损”。这一特点促使了该方剂的衍变,上述文中章节列举了各医家通过药物的加减化裁,衍生出了许多新的方剂。

再比如八仙长寿丸,亦称为麦味地黄丸,是明代龚廷贤所创,他在《寿世保元》中详细记载了这一方剂。该方由地黄丸加上麦门冬和五味子组成,具有补肾敛肺养阴的功效,常被用于治疗肺肾阴虚所致的咳喘、消渴等症状。
滋阴八味丸,又称知柏地黄丸,是明代张景岳所创,载于他的《景岳全书·新方八阵》。此方以地黄丸为基础,加入知母和黄柏,具有滋阴降火的作用,常用于治疗肾阴虚、相火旺导致的男子滑精、妇女崩漏带下以及急慢性肾炎等病状。
此外,明目地黄丸、归芍地黄丸、都气丸、杞菊地黄丸、肉桂地黄丸和耳聋左慈丸等,都是在该方的基础上,经过巧妙的加减化裁,衍生出的具有特定功效的方剂。它们分别针对不同的病症,如肾虚目暗、骨蒸潮热、肾虚呃逆、肝肾不足、虚火上炎以及肝肾阴虚等,展现出中医药治疗的灵活性和精确性。
这款古老的中药方剂,自问世以来,便以其独特的组方和卓越的疗效,赢得了世人的广泛赞誉。其组方精细,包含熟地黄八钱,山茱萸、干山药各四钱,泽泻、丹皮、白茯苓(去皮)各三钱,每一味药材都经过精心挑选,确保其药效的纯正与强大。
经过数百年的临床验证,此方的疗效确凿无疑,被誉为“补阴方药之祖”。历代医家对其配伍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尽管学术流派各异,但对其疗效的肯定却是一致的。

在方剂中,熟地黄作为主药,用量最大,补肾阴之力尤为显著。然而,它并非孤军奋战,山萸肉、山药的加入,为方剂增添了更多的补益之力。这三味药材合称为“三补”,而泽泻、丹皮、白茯苓则被称为“三泻”。这种“三补三泻”的配伍方式,既能够补益身体,又能够避免补益过度导致的偏胜之害。
在《医方集解》中,有言:“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阖一辟,此乃玄妙。”这正是其方配伍特点的最好诠释。方剂中虽然含有丹参、茯苓、泽泻等渗利活血药,但其用量较小,意在泄浊肾、渗脾湿、泻相火,以顺应肾藏精、主水之机。
综上所述,这个方剂不仅是一款补益剂,更是一款补肾剂。它以补为主,补肾阴为重,同时补中有泻,寓泻于补,实为通补开合之剂。这种精妙的配伍方式,使得其在中医界独树一帜,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方剂。
慢性肝病,这一医学难题,其根源常常与肝、脾、肾三脏的功能失调紧密相连。肝,作为五脏之一,其疏泄调达之性至关重要。然而,当肝病缠绵不愈,病程日久,便容易累及肾脏。这是因为,肝木一旦失去平衡,易于化火,火势旺盛则易耗伤肾阴,导致肝肾阴亏。这种病理变化,进一步加剧了病情的严重性,使得治疗更加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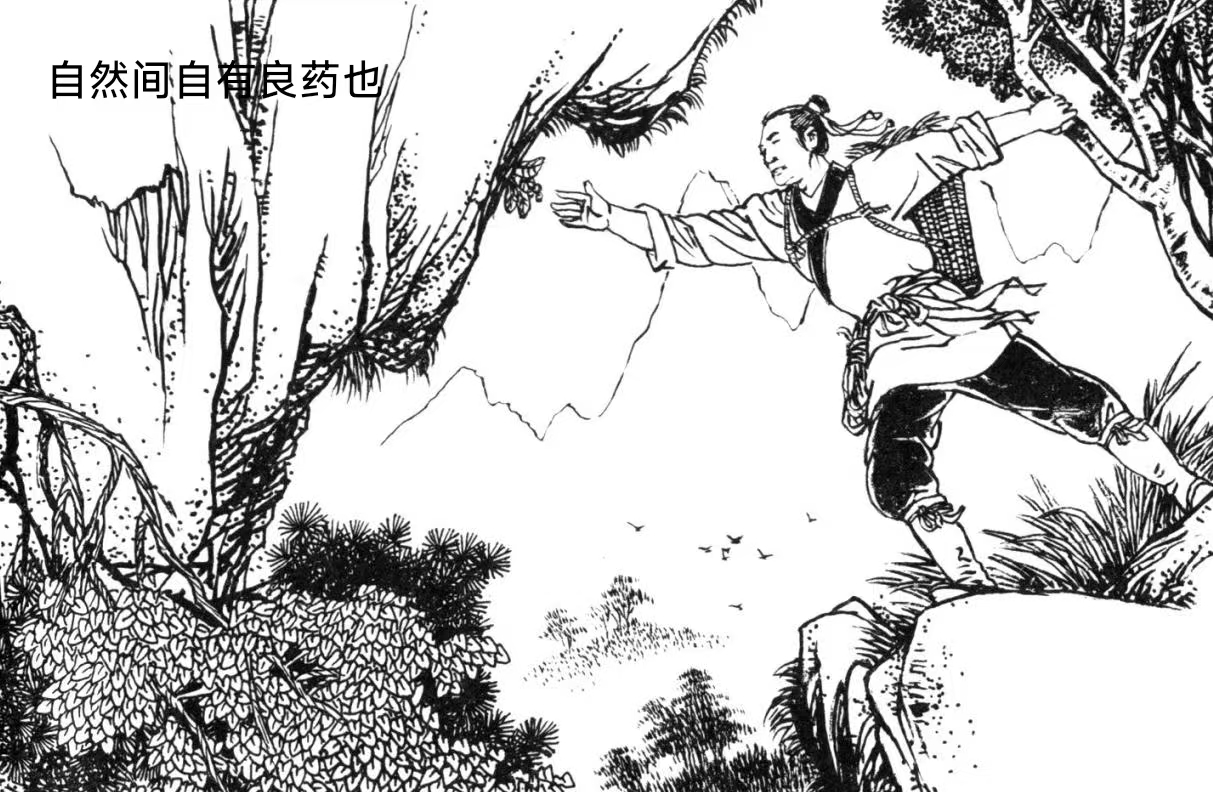
面对这一难题,笔者深入研读古代医籍,汲取前人的智慧,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认为在疑难肝病出现肝肾阴亏证时,可以依据“肝肾同源、异病同治”的理论,采用此方为基本方随证加减的治疗方法。这一历经千百年考验的经典方剂,具有滋补肾阴、养肝明目的功效。在随证加减的过程中,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灵活调整药物组成,旨在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在临床实践中,医者运用这一方法,治疗了众多慢性肝病患者,取得了显著的疗效。许多患者在使用其加减治疗后,不仅肝肾功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且整体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提升。这一成果,不仅验证了肝肾同源、异病同治理论的正确性,也为慢性肝病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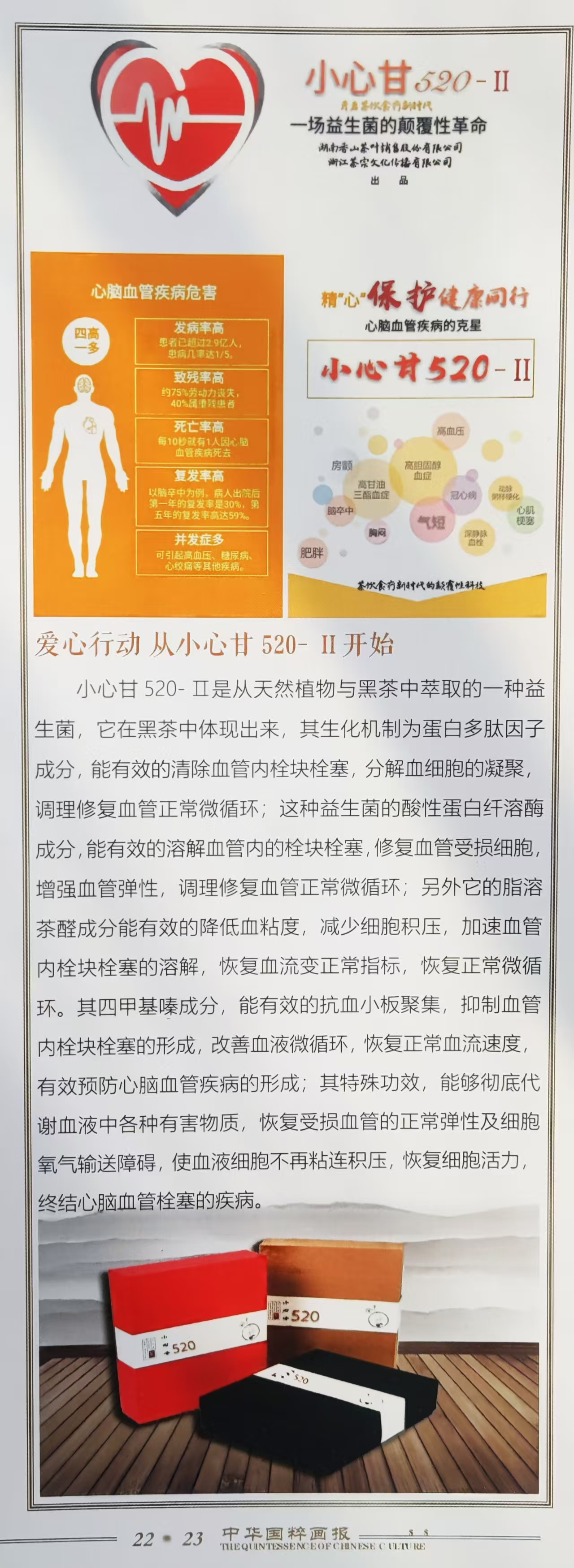
在这里再脑补一下什么是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中医学是辨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重视同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重视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种证,因此在临床治疗时,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来处理。
所谓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点,以及病人机体的反应性不同,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表现的证候不同,因而治法也不一样。
所谓异病同治,则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证候,因而可以采用同一方法治疗,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可见,中医治病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证的异同。相同的证可用相同治法,不同的证就必须用不同治法,即“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真可谓灵活辩证神奇至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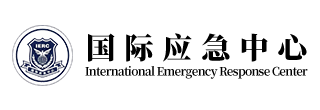

 全国免费客服电话 400 8749 119
全国免费客服电话 400 8749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