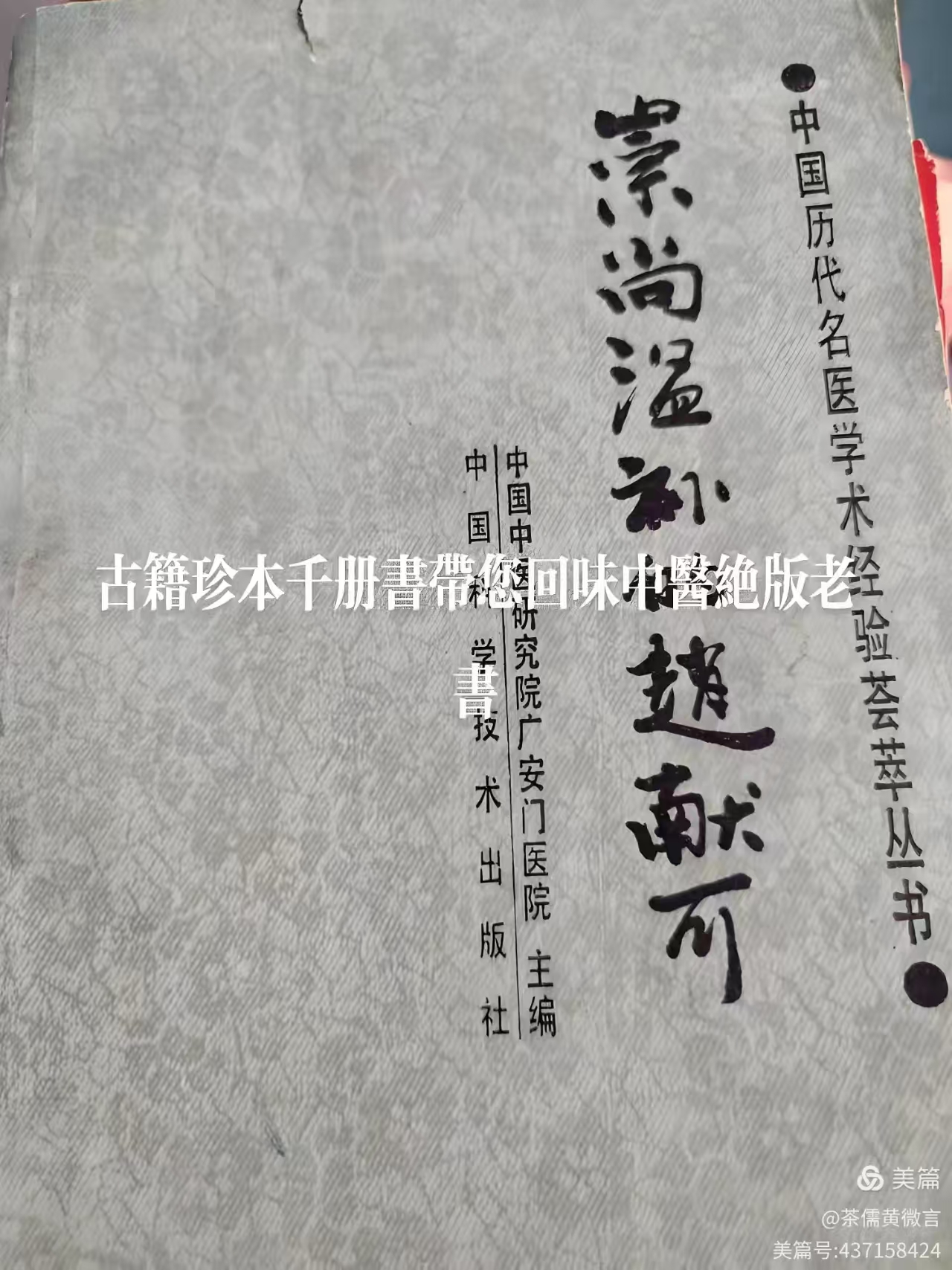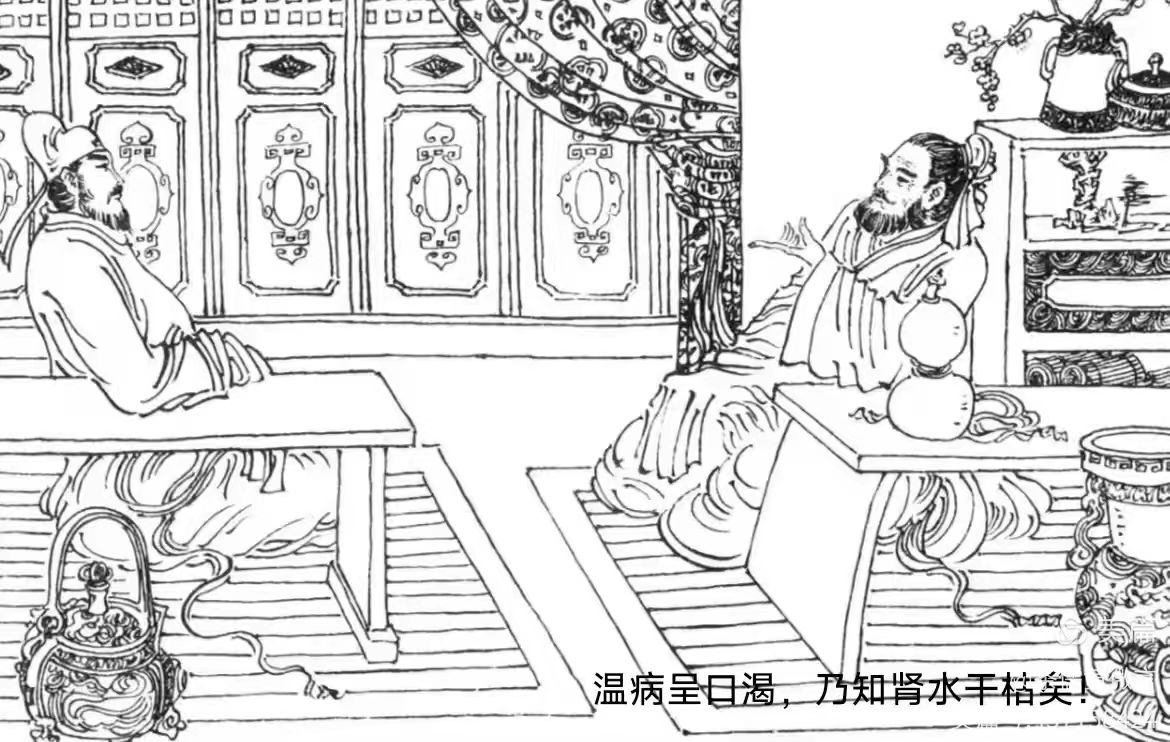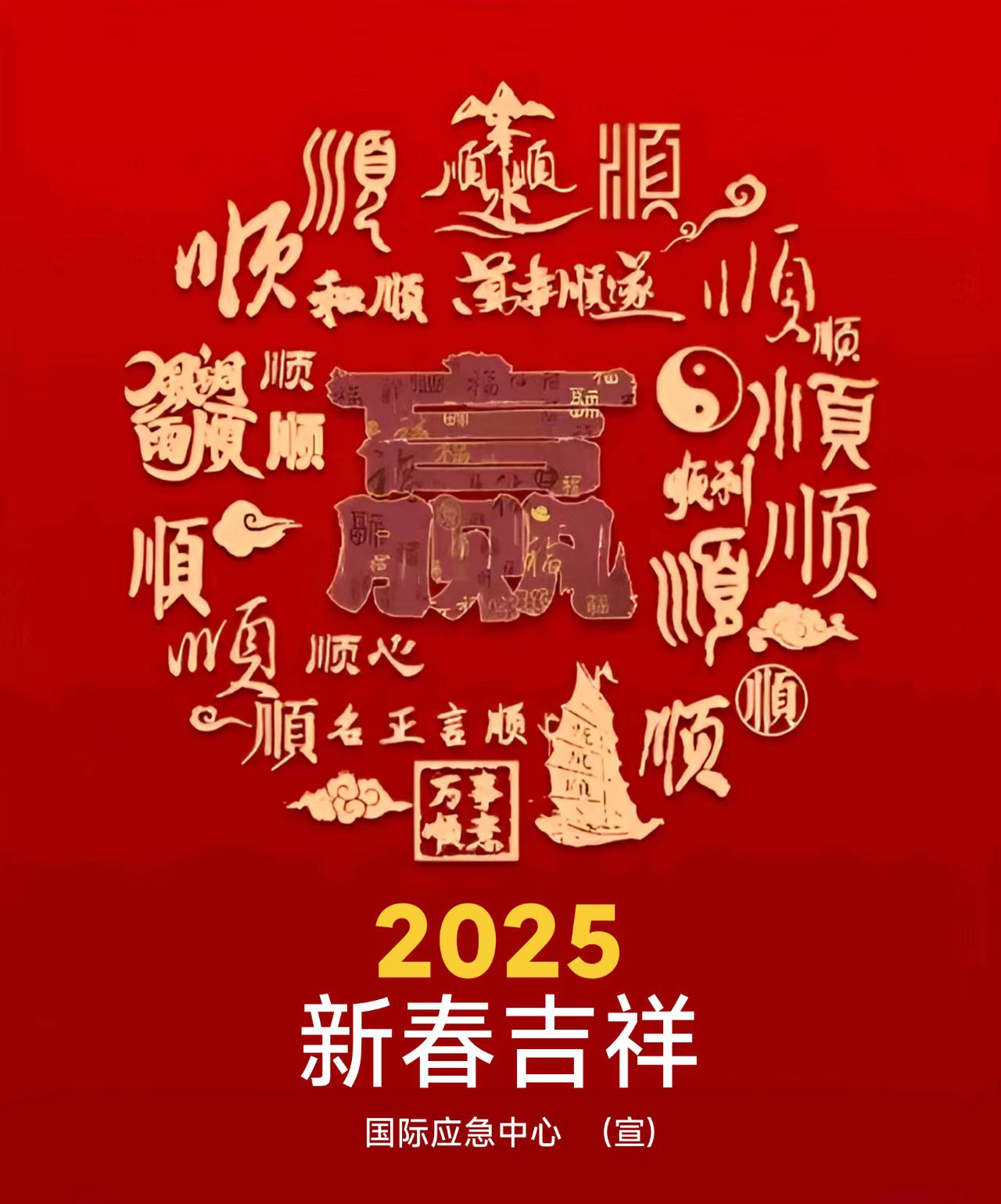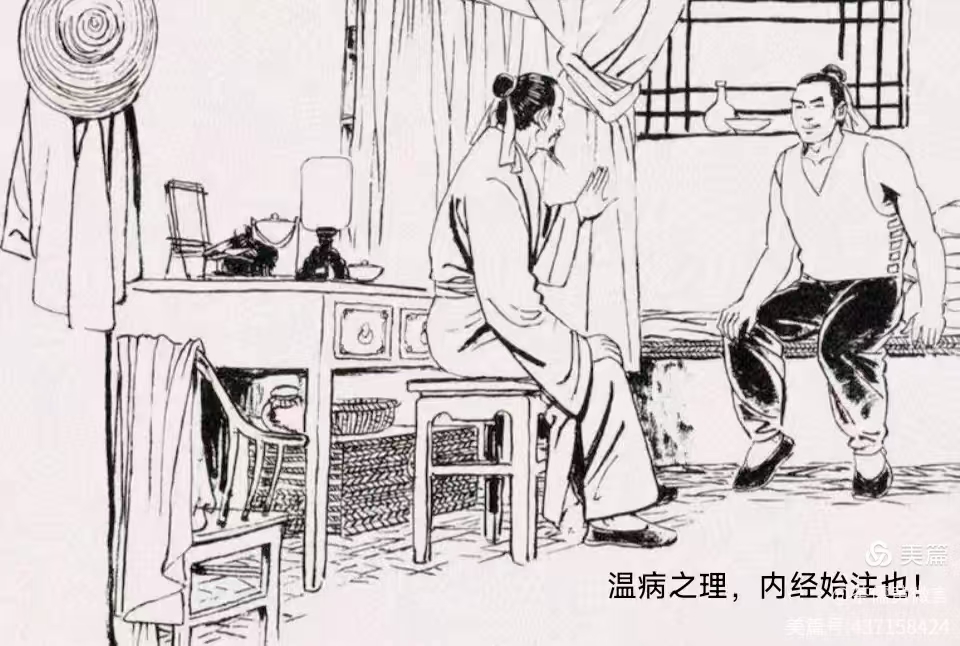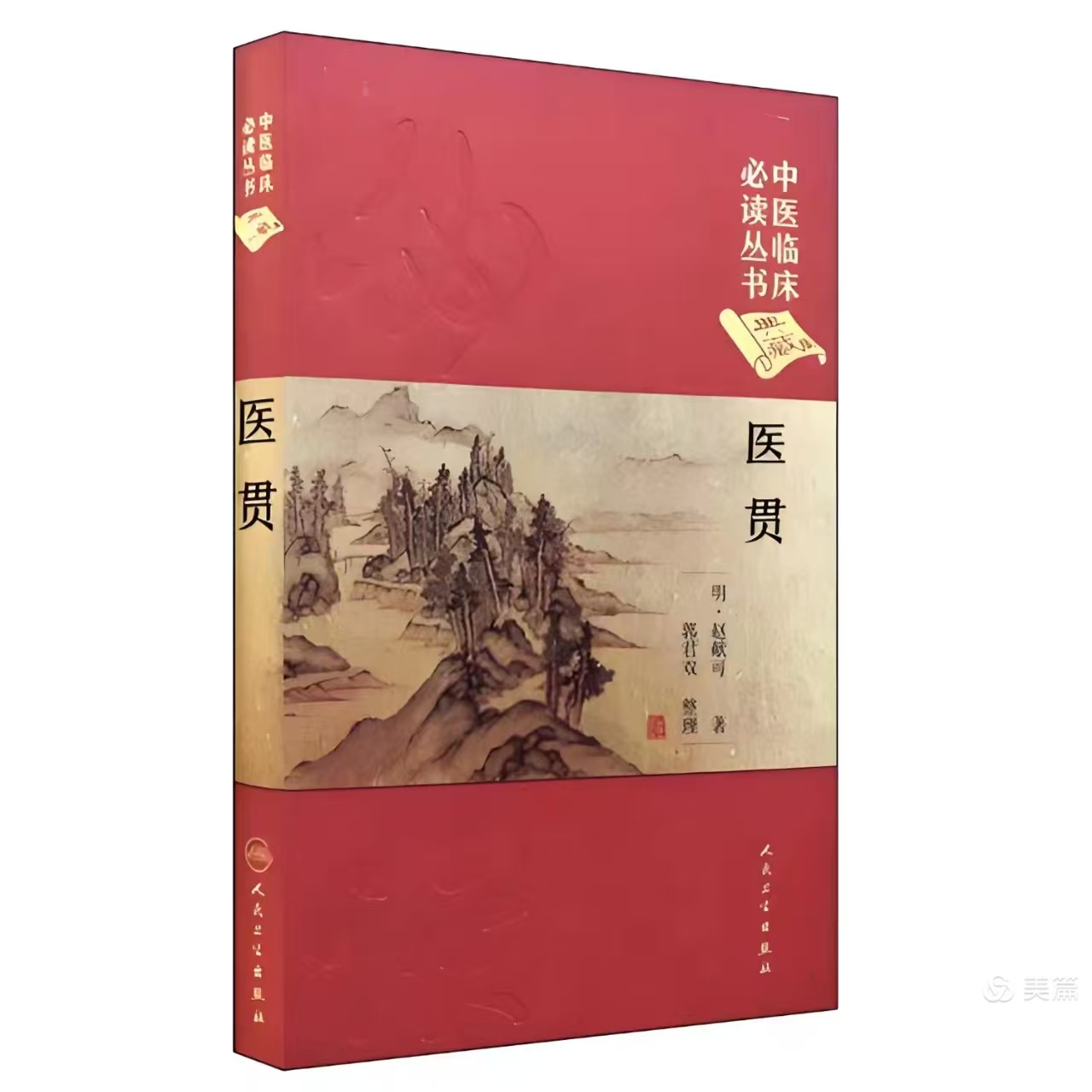第十章:
冬伤寒 春必温
病邪状 决体身
有恶渴 乃冷陈
加凉药 是守真
张子和 用六神
葵用药 六经本
火郁内 滋肾门
六加柴 效果神
内经考 原理真
此病毒 阴阳分
阳毒黄 阴青甚
升麻鳖 汤救人
注译:
“夫伤寒二字,盖冬时严寒而成杀厉之气,触冒之而实时病者,乃名伤寒”,夫,就是那个的意思,这就是问那什么叫伤寒?伤寒就是冬天严寒时候的“杀厉之气”,如果“触冒之”,也就是受了寒,“实时病”,就在这个时候刚受寒立即就病了,这叫伤寒。如果“不即发者”,没有马上犯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也就是,“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这是《黄帝内经》里边讲的,就是冬天伤了寒,寒毒藏在肌肤里。到春天发病,这叫温病,到夏天发病叫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暑病比温病更厉害一些。“既变为温,则不得复言其为寒”,已经变成温病了,就不能再说这是受寒了,即不能再说它是寒邪导致的疾病。这段话我个人不太认同,古人讲“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邪气伤了人以后,病邪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比如感染了某个病毒,不能说它在体内时间久了,就不是这个病毒了,它原来是寒毒现在变为热毒了,一定不是的。所以说病邪侵入人体后,它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人的体质会变化。所以感受到寒邪也可能表现出热证,因为与体质是相关的。所以是不是即时发病,发病以后是什么状况,还取决于病者的身体体质,整个病情状态实际上就取决于病邪和体质两个方面。

成为温病后就“不恶寒而渴者是也”,温病、暑病的特点是什么?它只是表现口渴,并不怕冷,冷只是之前的,其蕴于身已化为温,由冬而春,故曰冷于陈也。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里边也讲了这种症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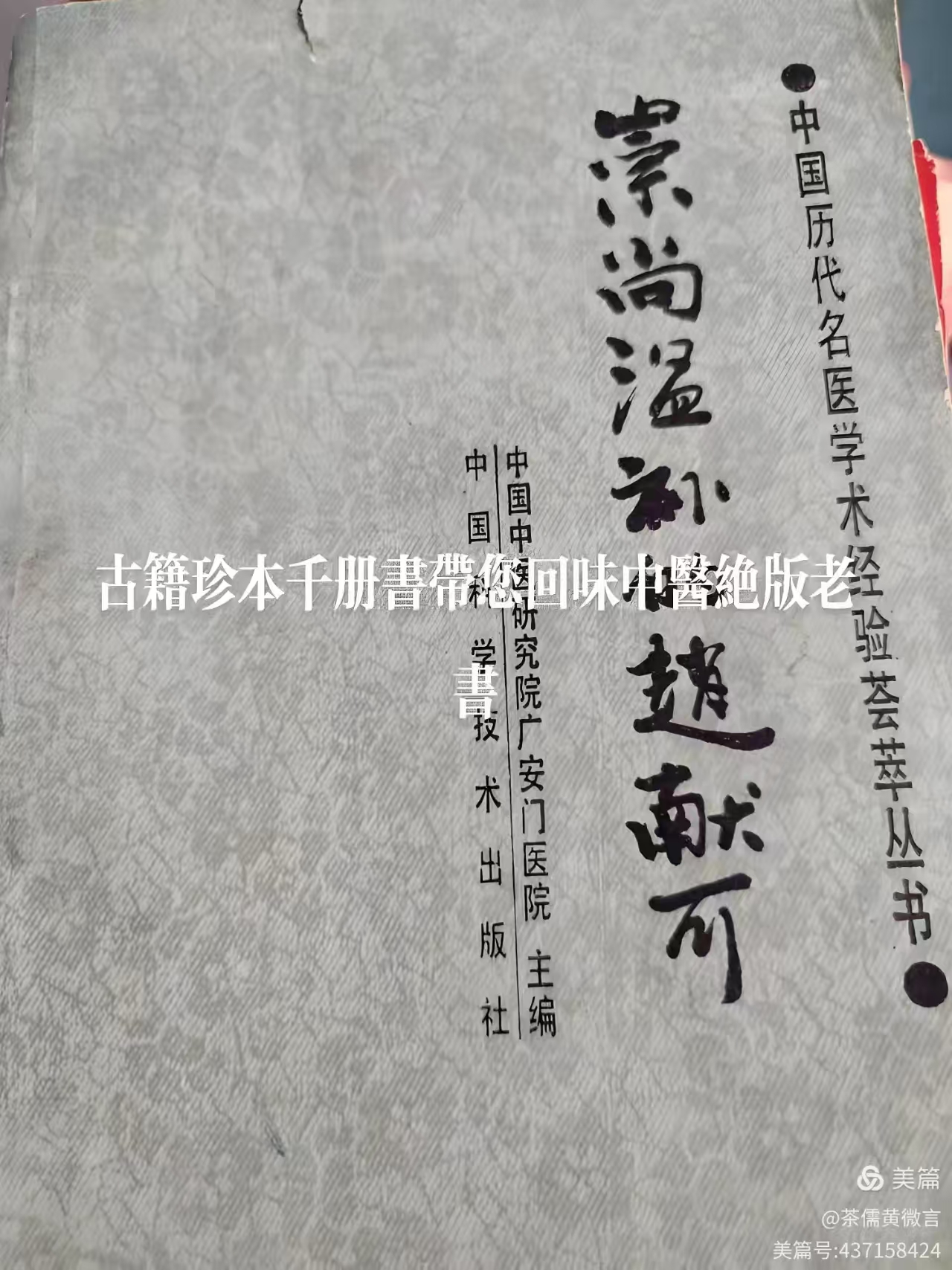
“其麻黄、桂枝,为即病之伤寒设”,现在受寒后即刻发病,用麻黄汤、桂枝汤。“与温热何与,受病之源虽同,所发之时则异,仲景治之,当别有方”,前面麻黄、桂枝治疗的是当下受寒就生病的这种伤寒。“与温热何与”,如果春天、夏天发病,受病之源虽同,但是所发之时不同。那么“仲景治之”,张仲景药治疗这类温病、暑病,应当还有其他方子。为什么没见到,他说“缘皆遗失而无征,是以各家议论纷纷,至今未明也”,他就想,张仲景既然讲了伤寒,当下的伤寒有方子,那么温病、暑病没有方子,是因为找不到了。所以后来各家议论纷纷,到现在也不明白。
“刘守真谓欲用麻黄桂枝,必加凉药于其中,以免发黄之病”,刘守真,就是刘河间,他是主张用寒凉药来治疗这种热病。他说在麻黄、桂枝这些方子里边加上凉药,就可以了,“以免发黄”,这类发热性疾病,伴有口渴,如果不加凉药,病人可能发黄。发黄是什么?就是黄疸。实际上刘守真讲的是有道理的,感染肝炎病毒后,不一定马上就有表现,但是等有表现的时候,要是不用凉药,肝病加重,病人可能真的就出现黄疸,所以这是符合实际的。“张子和六神通解散,以石膏寒药中,加麻黄、苍术,皆非也”,金元四大家中张子和是善用吐、下的方法来治病的攻邪派。他用六神通解散,在他的书里边可以看到,用石膏这些寒药,再加上麻黄、苍术,“皆非也”,赵献可认为他这种治疗方法也不妥当。
“盖麻黄、桂枝辛热,乃冬月表散寒邪所宜之药”,麻黄、桂枝这些辛热的药,适合用在冬天受寒以后,不宜用于春夏之时。这就是赵献可说,麻黄、桂枝在温病、暑病里尽量就是不要用了。“陶氏”即陶坚,“陶氏欲以九味羌活汤,谓一方可代三方,亦非也”,陶氏有张方子叫九味羌活汤,在方剂里边还作为一个重点方剂,应该是让大家背过。为什么说“一方可代三方”,这一个方子可以治疗三阳合病,太阳、少阳、阳明三阳合病,受寒以后入里化热,用一个九味羌活汤就够了,不用选麻黄、桂枝、柴胡等,这个方子就足够。赵献可说,“亦非也”,也不对。“羌活汤易老所制之方,乃治感四时不正之气”,易老应该是张元素,它治疗什么?“四时不正之气”,什么叫四时不正之气?冬天大寒节气时认为冷,这叫四时不正之气吗?不叫。这是四时应当有的气。
春天应该是温而反寒,这就是四时不正之气,该暖和了不暖和反而冷,这就叫四时不正之气;“夏宜热而反温”,夏天应该很热,气候却不是很热;秋天应该凉反而是热;冬天应该寒,反而是暖冬。这都叫“四时不正之气”,羌活汤就是治疗这些疾病的。
这一段讲的温病的治法,前人的一些论述以及赵献可的观点。
“又有春夏秋三时,为暴寒所折”,就是春天夏天秋天,“暴寒”就是突然受寒。“虽有恶寒发之证”,没有冬天寒得那么厉害,所以也不需要用麻黄、桂枝来散寒,用辛凉之药,因为有辛味的药能够散就可以了。“通内外而解之,况此方须按六经加减之法,不可全用”,用上麻黄、桂枝,也要按六经的特点来进行加减,也不是全部都用上,但是不如用逍遥散好。也就是说你用麻黄、桂枝加减,不如选逍遥散,到后边讲郁病的时候,他尤其强调。“真可一方代三方也”,用逍遥散后,麻黄、桂枝、柴胡这些方子就都可以代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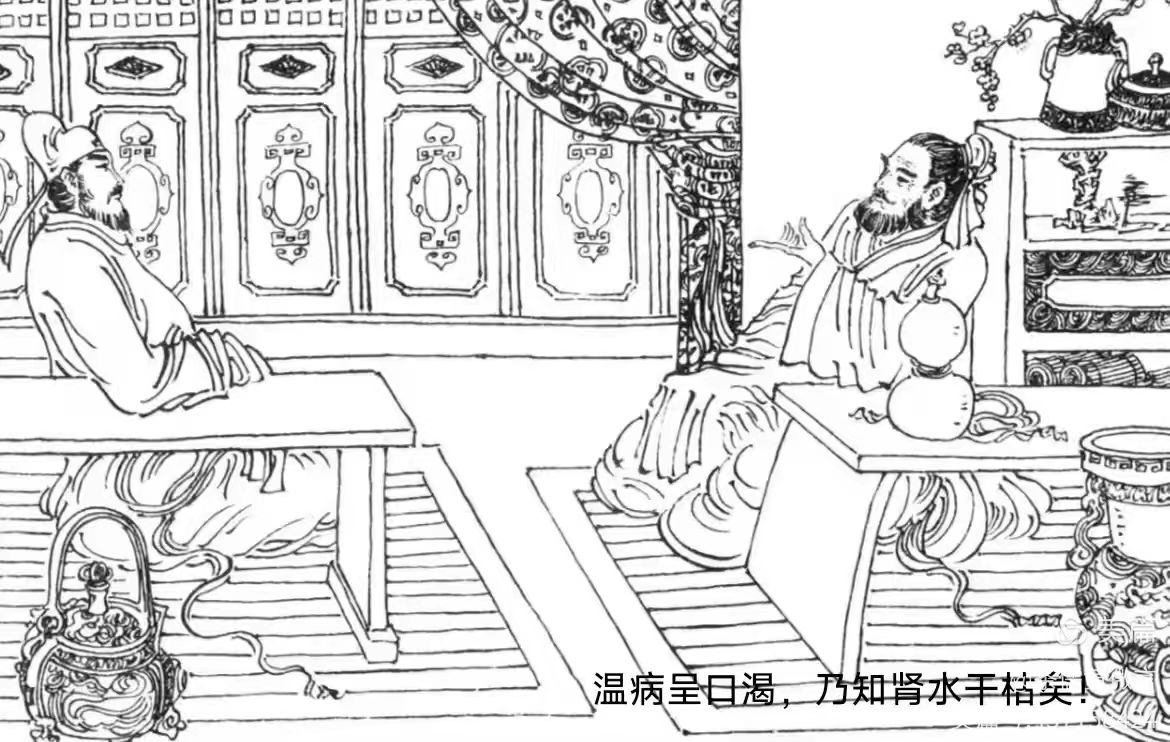
温病为什么出现口渴?“则知肾水干枯矣”,赵献可最终还是要归到肾,说是肾水干枯才出现了渴。“盖缘其人素有火者,冬时触冒寒气”,这就说明什么?这个人平素就是个热性体质,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火底子”,如果“冬时触冒寒气”,感受寒邪,“虽伤而亦不甚”,虽然伤了寒也不会很厉害。“惟其有火在内,寒亦不能深入”,是因为体内阳热比较盛,所以说寒邪进得不深,“所以不即发”,不会一受寒邪马上发病。“而寒气伏藏于肌肤”,没有马上发病,又没出来,那是到哪了?是“伏藏于肌肤”,这是古人讲的,把肌肤理解成什么?不要理解成皮肤和肌肉,只是病变比较表浅轻微,它还没有到能够引起非常严重疾病的程度。“自冬至三四月,历时既久”,病邪潜伏在体内三到五个月的时间,时间长了。“火为寒郁”,外有寒邪,内有火热,这就叫“火为寒郁”。“中藏亦久”,在体内藏的时间长了,“将肾水熬煎枯竭”,也就是体内的火郁在里边,反而把肾水给煎熬枯竭了。他在讲为什么出现所谓的“温病”的原理。

此“发热而渴”的表现,“非有所感冒也”,这个感冒和现在说的感冒不一样,不是感受了什么样的热邪或者是寒邪,不是新感,而是原来肾水被耗竭了。“海藏”,这是医家王海藏,“谓新邪唤出旧邪,非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王海藏说,这个时候的温病,是因为新感受外邪,把里边的邪又唤醒了。“若复有所感,表又当恶寒矣”,赵献可就说了,如果确实是“复有所感”,又外感了邪气,那么又应该出现恶寒,可是前面说了口渴无恶寒,所以说它不是有新感。“余以六味地黄滋其水,以柴胡辛凉之药,舒其木郁,随手而应”,赵献可遇到这种情况就用六味地黄先养肾水,因为说郁在体内的火把肾水给耗竭了,他就用六味地黄滋肾水,然后“以柴胡辛凉之药,舒其木郁,随手而应”,实际上就是柴胡六味地黄。当遇到温病,春温、暑温的时候,与其用麻黄、桂枝加凉药,不如用六味地黄加柴胡,上面整个内容讲的就是这个,而且他讲效果是随手而应,一般医生可是不敢这样讲话的。他既然这么讲了,我认为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在临床上我也没有经验,没有用六味地黄去治疗温病。但是我认为赵献可讲的还是可信的,以后我们遇到了温病,如果是热性体质,一派热象的出现,不恶寒反而口渴的,我们不妨这么一用。而且用的时候,这个我们临床经验我们是有的,柴胡的量一定要用足,用到30g,那么这个热就很容易退掉。因为有六味地黄,渴也会解决得好。
这个方子到底有没有效果?赵献可讲了,这是他的体会,“此方活人者多矣”,就是说我用这个办法治好的病太多了,“予又因此而推展之”,我又在这个基础上把它扩展开来,用于更多的疾病。“凡冬时伤寒者,亦是郁火证”,他说冬天伤寒其实也是郁火。“若其人无火,则为直中矣”,如果体内要是没有火的话,那他一定是直中,什么是直中?上次咱们讲的,直接是胃肠道感染,导致的拉肚子。如果体内没有火的话,不会表现为伤寒,它会是直中。“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肌肉而腑脏”,上次咱们讲过了,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这样传变。“今人皆曰寒邪传里,寒变为热,既曰寒邪,何故入内而反为热,又何为而能变热耶”,这句话我认为非常好,很多人都说寒邪入里化热,实际上寒邪不能够变为热,“寒邪,何故入内而反为热”,他就说寒邪进体内应该是寒性,怎么能表现出热来呢?所以他认为热是内生的。“又何为而能变热耶”,寒邪怎么能变热的?“不知即是本身中之火,为寒所郁而不得泄,一步反归一步,日久则纯热而无寒矣”,本来体内有热,如果受了寒,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伤寒”,这个伤寒的人本身内部有热。“所以用三黄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即火郁发之也。三承气,即土郁则夺之。小柴胡汤,木郁达之也。其理甚简而易,只多了传经六经诸语,支离多歧”,既然是内热,就用三黄解毒,升麻、葛根、三承气,就可以把火去掉,小柴胡汤也是木郁达之,这里边道理都很简单,只是因为有了那么多传经的说法,结果出现那么多的分歧,大家争论很多。赵献可能把这个事情,连伤寒本身都当成是“内有郁热,外受寒邪”这么来理解,这篇讲完了,他后边正好要引导到他下一篇文章《郁论》里边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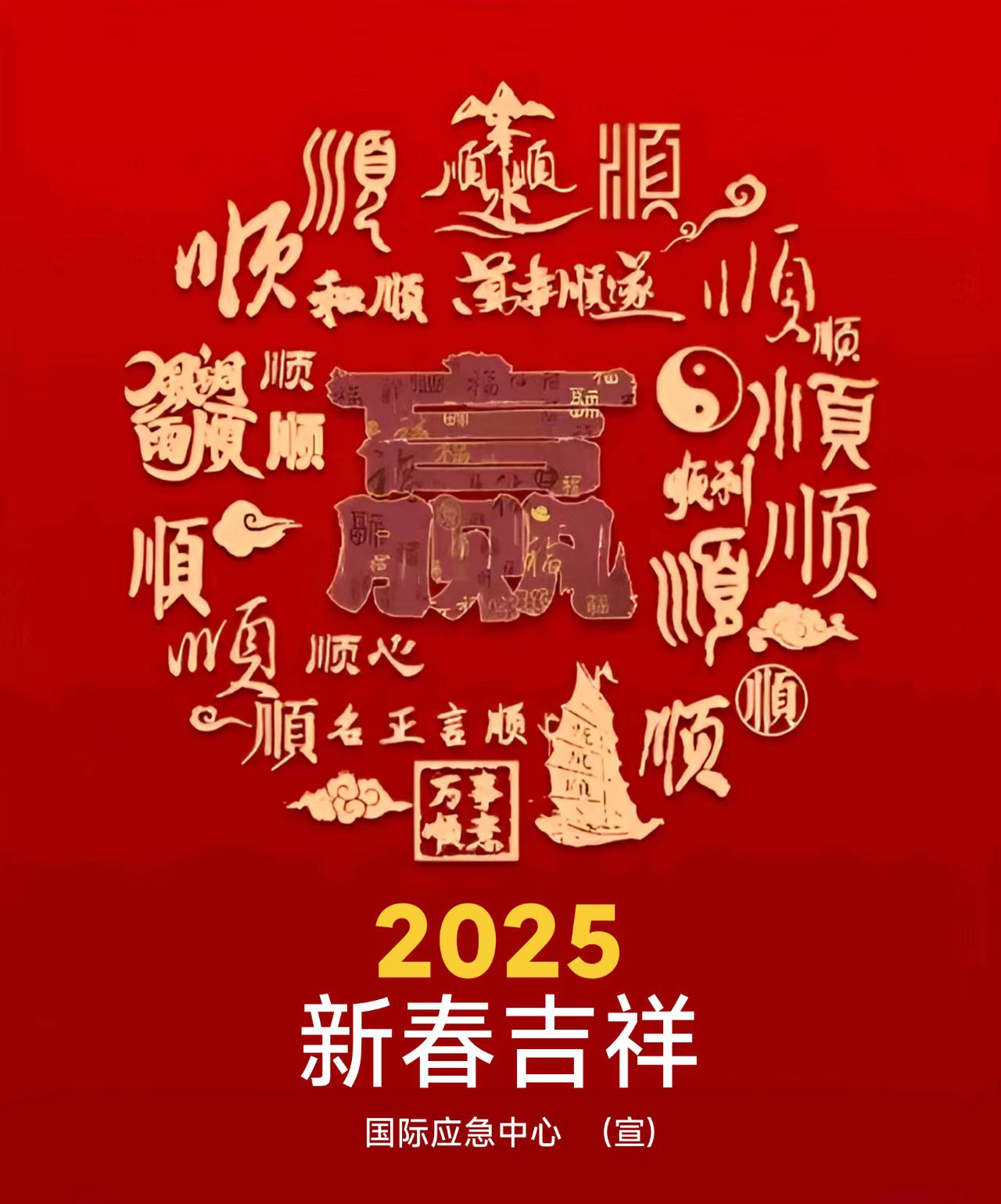
赵献可又说“凡杂证有发热者,皆有头疼、项强、目痛、鼻干、胁痛、口苦等证,何必拘为伤寒”,也就是我们一般的内伤杂病,也有发热的,可以出现这么多的症状:头痛、脖子痛、眼睛痛、鼻子干、胁痛、口苦,“何必拘为伤寒”,为什么都要把它们当成伤寒去对待。“局伤寒方以治之也”,局限在伤寒方里边来论治这些病。“余于冬月正伤寒,独麻黄桂枝二方,作寒郁治,其余俱不恶寒者,作郁火治,此不佞之创论也。”只有冬天真正的伤寒,用麻黄、桂枝两方。“作寒郁治”,就是治疗寒邪郁闭的方子,其他不恶寒的都当作郁火来治疗。“此不佞之创论也”,什么叫不佞,高中学古文都学过的,不佞是一个谦卑的说法,指的是自己,即这是我的创论,这是我提出来的新的见解。“闻之者孰不骇然吐舌”,听到以后,大家很惊讶,怎么能是这样呢?“及阅虞天民《医学正传·伤寒篇》云”,等读到虞天民《医学正传·伤寒篇》说,“至人传曰:传经伤寒,是郁病。余见之,不觉窃喜,以为先得我心之同然”,在虞天民的《医学正传》里边,“有至人传曰”,高人说过,“传经伤寒”,所谓的伤寒传经,实际上是郁病,赵献可看到《医学正传》里边讲的这句话,“不觉窃喜”,就是暗暗高兴,“以为先得我心之同然”,原来人家书里边就已经与赵献可的观点一致了。
“及考之《内经》,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岐伯曰:寒气外凝内郁之理,腠理坚致,玄府闭密,则气不宣通,湿气内结,中外相薄,寒盛热生,故人伤于寒,转而为热。汗之则愈。”从《黄帝内经》里边去考证,“人伤于寒,转而为热”是怎么回事?黄帝问是怎么回事?岐伯,就是与黄帝问答的名医,说“寒气外凝”,寒气从外伤及到人,然后导致内郁,内在的阳气郁闭。“腠理坚致”,皮肤比较致密,“玄府闭密”,也不出汗,皮肤抵抗力还好。“则气不宣通”,气郁闭在里了。湿气也出不来,就“湿气内结”。那么“中外相薄”,就是正气和外邪相搏斗时,“寒盛热生”既怕冷,又发热。“故人伤于寒,转而为热”,就是说虽然是受寒,但表现出的是热。“汗之则愈”,用麻黄、桂枝这些药一发汗就好了。“则外凝内郁之理可知”,寒邪外凝在肌肤,阳气内郁在里,这你就知道了,原来《黄帝内经》里边也是这么讲的。“观此,而余以伤寒为郁火者,不为无据矣”,看到这个后就知道,我说的伤寒是郁火,不是臆想出来的,《黄帝内经》里面讲过,《医学正传》里边也讲过,只是后来这些书没把这个事讲明白。“故特著郁论一篇”,就是专门下一篇我们要讲的郁论。在温病里边,他又讲,“论阳毒阴毒”,《金匮要略》里边说,“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这是《金匮要略》里边讲的阳毒病。阴毒病,“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死生如阳毒”,这不是《金匮要略》原文,我记得这是用升麻鳖甲汤加减,引用比较简略。“《千金》云:阳毒汤治伤寒一二日,变成阳毒,或服药吐下后,变成阳毒,身重腰脊背痛,烦闷不安,狂言或走,或见鬼神,或吐血下利,其脉浮”,这是讲阳毒更严重的。阳毒之为病说“面赤斑斑如锦纹”,有的大黄叫锦纹大黄,是吧,什么是锦纹?就是织的缎子,我印象中苏锦,有各种颜色的。锦纹大黄花纹好像与绣的一样,我们叫“锦上添花”。它本身就是个花布,然后再加上花不就更漂亮,“面赤斑斑如锦纹”,就是脸上就像绣的花一样,首先是红的,然后是一片一片的,像绣上去的,这是阳毒病的一个特点。而且还有咽喉痛,唾脓血,这显然是咽喉部的化脓性感染。这种感染有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咽炎,还见于猩红热。那阴毒呢,面目青而不红,身痛得厉害,就像“被杖”,就是被打过了,身痛剧烈,咽喉痛。上文所述阳毒黄,阴青痕,这是直观的一个表现。其实这两种病实际上就是两种体质,一种是阳盛体质的化脓性感染,一种是阳气不足的化脓性感染。阳气不足表现出来就是疼得厉害,体内的热比较重的就“面赤斑斑如锦纹”。但不管体质状态怎样,感染的病邪是一样的,所以都用“升麻鳖甲汤并主之”,也就是这两种病都能用升麻鳖甲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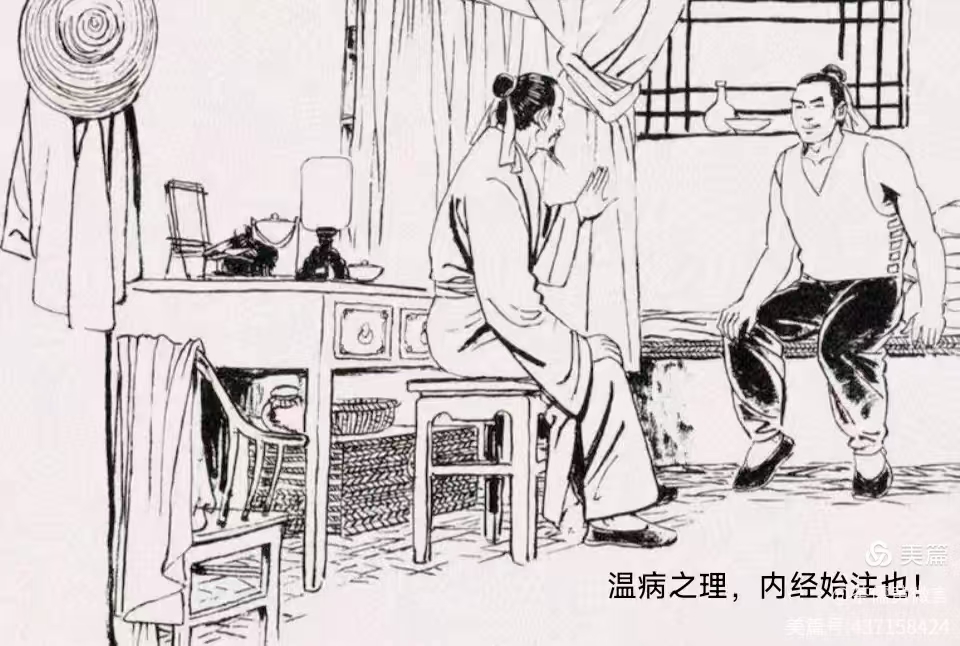
这就提醒我们升麻鳖甲汤是干什么的,是针对病因的,是针对病原微生物的。在温病里边,用升麻都很多。李东垣也是柴胡、葛根、升麻这么用,就是对于这种外来的热毒,升麻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下边说是“伤寒一二日,变成阳毒”,或吃药以后变成阳毒,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推测。本来他就感染了,然后表现出阳毒导致的身重、腰脊背痛及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导致的烦躁不安、狂妄、或见鬼神,这就是谵语,还可以见到消化道感染的吐血下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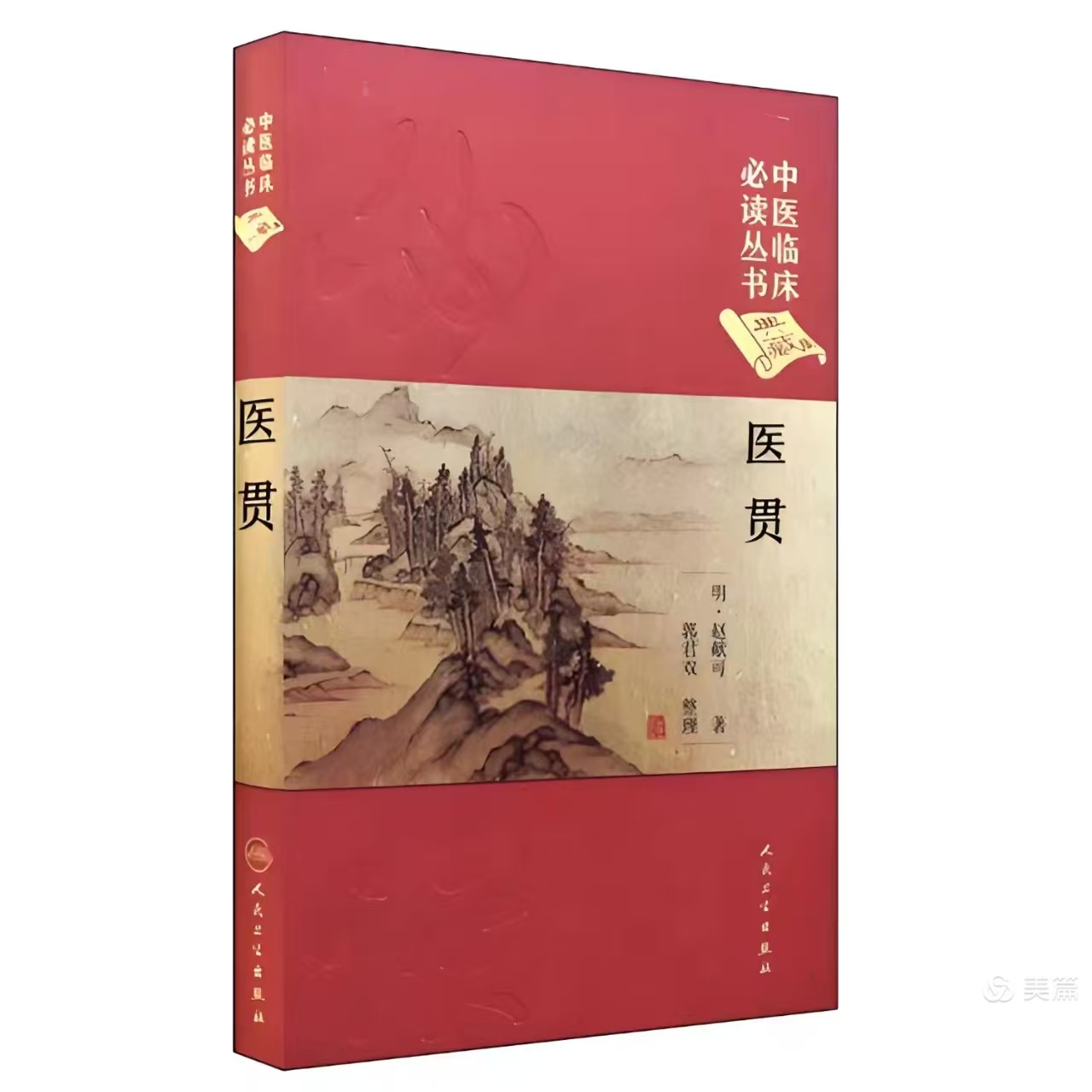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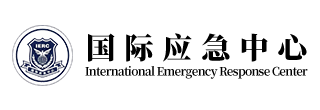

 全国免费客服电话 400 8749 119
全国免费客服电话 400 8749 119